《第4話:Me Without You》
[82] 湖都擁有了天的流星,多美好。
[2021年10月17日]
一星期過去,沒有事情發生。
沒有集體失憶的同學。
沒有從天而降的冰箱。
沒有全職搶劫的柴犬。
當然,沒有「記憶信貸」。
我本正打算告訴自己,上週只是場荒謬的夢。
直到今天。
接下來要跟你說的三件事,簡直只有「做乜鳩」能形容。
⦾
「做乜鳩」首部曲:搭巴士。
週一日研課遲到0.0001秒會被視作遲到,所以我每個早上泡完熱騰騰的茶後,定必準時下樓候車。我家位處72M巴士第2個站附近,因此駛來的幾乎都是空車,我亦從未試過擠不上巴士。
而今天,從總站駛來的72M,竟像沙甸魚罐頭般塞滿乘客。真正荒謬的是,我瞧見車裏的逾百位男性乘客,無論坐著站著,外貌都99%神似--深藍色帽、俊俏外貌、瞇眼微笑。唯一差別,只在於裝束不同。
假若是兩三個這樣的人,尚可解釋是雙胞胎、三胞胎。但上百個呢?《智能叛變》嗎?啊,那倒說得通了。
搞什麼,是社會實驗還是電視台惡搞之類的?
我瞄著手錶,時間尚早,還夠時間多等2班車。
第2、3班巴士駛走了。情況跟第1班一樣,上百個樣貌99%相同的男人,把車廂擠得水洩不通。
排在我前方的良好市民,一律粗口橫飛地離隊,濃妝OL跟地盤工人截了的士離開,拖鞋阿叔致電巴士公司投訴有廢青惹事生非,抹煞他準時上班的理想。
坦白說,我同樣焦躁,很想擠上巴士車廂,質問那幫傢伙在搞什麼鬼。但當務之急是準時上課,要先想方設法抵達課室。
更何況,我是心慌多於焦躁,因為那些傢伙頭戴的貝雷帽,款色跟12號和芊柔穿戴的一模一樣。難道又是「公司」搞的好事嗎?
為免遲到,我立馬轉乘小巴至語大火車站。李煘徐樓位於半山校園,火車站位處山下,因此我需要在火車站轉乘校巴,絕對是爭分奪秒。8:24,我拼盡九牛二虎之力,奔至準備開車的校巴前,伸手把正關閉的車門卡住了。
車廂只有車頭一排二人座位空著,我坐到窗邊位置,抹著汗喘著氣。司機是街知巷聞的「燥底巴士佬」,外表、聲線和語氣均酷似人氣KOL「燒山」,只是身材胖幾個碼。他在我「撬開」車門後就用「係!各位網友」的聲線詛咒個不停,說誰敢再阻他開車就劈誰!然後把車門再次關上──
門又被卡住了。
我連忙掃視「燒山」駕駛座旁有否菜刀、電鋸之類的──
步上車廂的是她。
那件脹鼓鼓的大衣,那本夾著刀片的《挪威的森林》。
程雨奈仍是那副「幽靈公主式」的怒容,使我聯想起「Cumulonimbus」。那是百科全書Wiki跟我提及過的學名,中文譯作「積雨雲」,意指龐大厚重的氣流雲,隨時會降下傾盆大雨。
對,她就像朵Cumulonimbus,變幻莫測。
程雨奈的右臉貼了塊透明膠布,我瞥見膠布裏頭的瘀腫,難道是上週被書撞到造成的傷口嗎?可是怎麼……
程雨奈掃視車廂,看著全車唯一空位──我的側旁,然後與我對視。
她眉梢顫動。
像是期許著什麼,卻又要把萬物拒諸門外。
我好幾秒後才懂啟齒:「程──」
她轉過身,下了車。
什──麼?!
「嘿!啲廢青都運鬼吉嘅你老味,邊個再阻我開車就劈到佢冚家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燒山」又怒又笑,巴士隨引擎咆哮駛動。
我又解鎖了一個全新的人生陰影。
我想向後座借塊鏡子,審視一下人到底醜成什麼程度,才會讓女生寧願等下一班車,都不肯坐你旁邊!
「你——搞——呢——場——惡——作——劇,為乜?」
她討厭我嗎?是因為上週的「惡作劇」嗎?是因為她認定我吃她豆腐嗎?
天下間,還有更委屈的冤案嗎?!
⦾
「做乜鳩」二部曲:木村拓JOY。
我順利提早抵達Lecture Hall 1,Wiki透過訊息通知我,他和哈士奇擠不進校巴無法上課,只託我幫忙檢查佛地摩的T-Shirt有否前後倒轉來穿——那是他倆今堂的賭注。
我凝視佛地摩脖子下TShirt的h&m尺碼牌,陷入沉思。早晨8時許,校巴理應空空如也,怎會如此多人乘車?
我獨坐第10排左側數起第2個位。扭開了熱水壺,才準備把茶灌進嘴裏──
熱水壺被奪去。
我瞧著不知從何而來的男人,把熱水壺倒轉猛力揮灑,直到我右側的整排座位都被淋濕。順帶一提,這次是中村藤吉的抹茶粉,味道還不錯喔。
「吓。」我目瞪口呆盯著男人。
他年齡貌似二十尾,頭戴深藍色貝雷帽、穿著Smart Casual衣裝,身高1米8左右,纖瘦而手腳修長,輪廓五官異常地好看。
如你所見,他跟擠滿72M巴士的那數百個「乘客」,外貌一模一樣。
沒錯,他酷似年輕時期的木村拓JOY。起碼90-92%像。
他把茶倒得一滴不剩,然後把熱水壺塞回我僵硬的手中,還幫我把手指合實。他朝我瞇眼一笑,慢條斯理地從後門離開,有幾秒我還期待他會像Gatsby廣告中那樣轉幾個身。
好吧,木村君,挺有禮貌的嘛。
由於荒謬絕倫,我幾秒後才恢復理智,氣憤站起要追趕那傢伙,心想要打他100頓怎樣的。
但我才剛邁步,程雨奈已身處第10排的右側樓梯位置。她掃視被淋濕的十數個座位,然後走近我。
最後一排的空位,只剩我及左右兩側,合共3個位置沒濕。
我拋低手中的熱水壺:「唔係我淋濕啲座位,係──」
「飯──凡天宇。」
我意料不到,她竟記得我的姓名。
「答我,我係邊個?」
我凝望著她頭頂那朵灰黑的Cumulonimbus,如芒刺背:「……程雨——」
「我,助教。」
「……係。」
「你,學生。」
「係。」
「就係咁樣嘅關係。冇其他。」
「非常好。」我才不想有「其他」什麼的!
「係咁。」她緊咬下唇,從我右邊座椅撕下一張白紙,捏成一個球原地丟下。我撿起紙團並攤開之,看見黑墨書寫的潦草。
雨奈,Sit!
By FTY飯添魚
「人生困難模式」的提示音,在頭頂鏗鏘響起。叮——
「FTY」又是什麼鬼?!
程雨奈坐到前一排的最右側,沒再瞧我一眼。
我在她眼中,肯定已非癡漢那麼簡單。
簡直是『究極之姐控』。
我已能想象,課堂習作的成績,被她寫上D或F的分數……拜託不要呀,我不要重讀!




 之後嘅Chapters就會揭曉
之後嘅Chapters就會揭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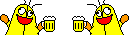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