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算
出道時候算係 “先鋒派“,實驗味道較濃
活著已經算“寫實”
你可以試下哈金本《戰廢品》
[書蟲]你最近睇緊咩書?8
笑聲裡找不著怯懦
1001 回覆
54 Like
3 Dislike
想大家睇第二次既超展開劇情
呢個作者之前有本幾特別既散文集,Levels of Life ,由熱氣球既歷史講到佢自己喪妻之痛,都值得睇(fyi, it's quite a short read )

呢個作者之前有本幾特別既散文集,Levels of Life ,由熱氣球既歷史講到佢自己喪妻之痛,都值得睇(fyi, it's quite a short read )
之前買左《行為》但睇唔到一半就放棄左

好似幾正 聽日撘車睇
其實都係貪佢夠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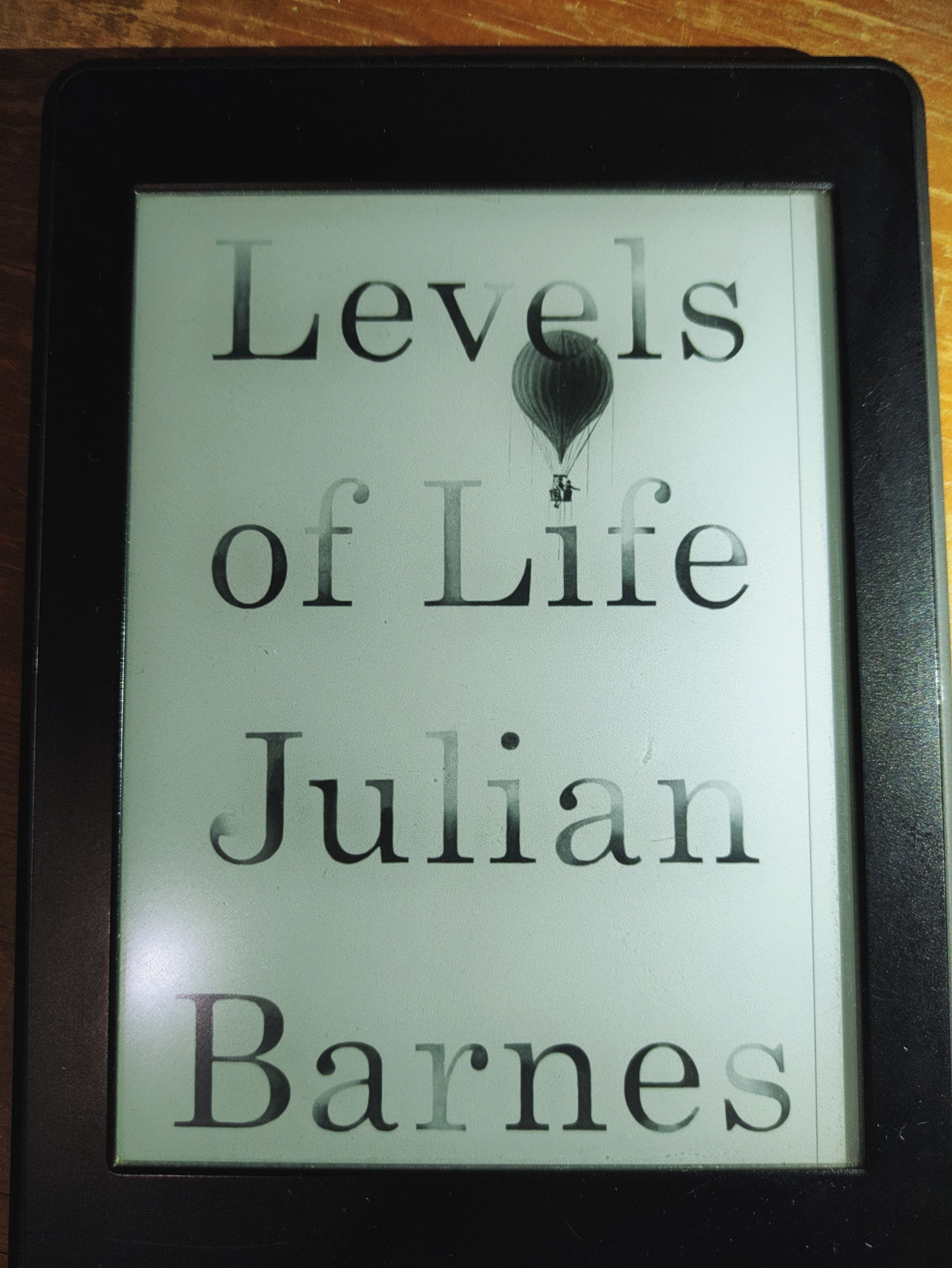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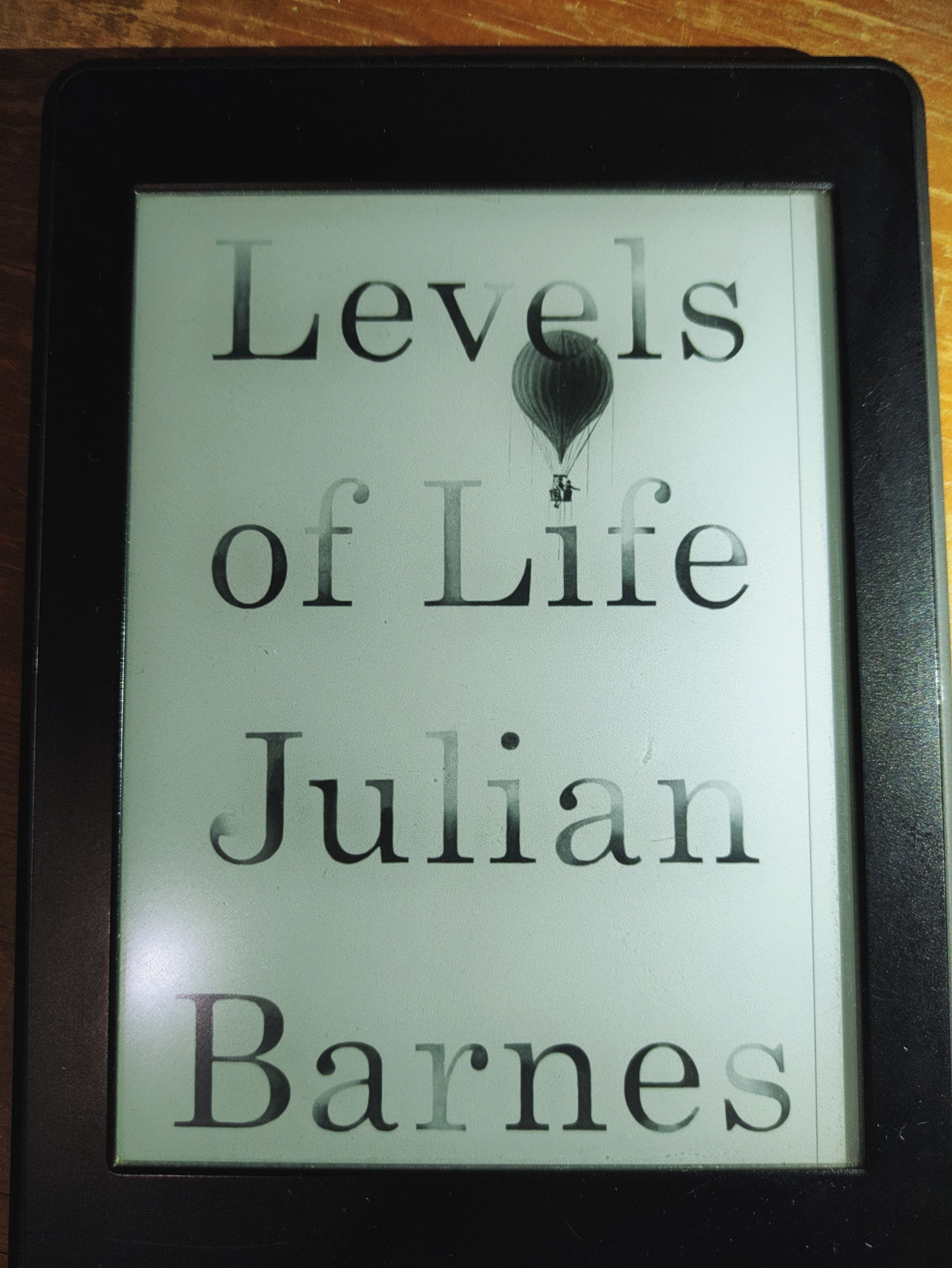
你本身係咪讀哲學系 因為我純粹出於興趣自己睇哲學書 冇接受過任何哲學課程 所以唔敢睇原著
因為我純粹出於興趣自己睇哲學書 冇接受過任何哲學課程 所以唔敢睇原著
 因為我純粹出於興趣自己睇哲學書 冇接受過任何哲學課程 所以唔敢睇原著
因為我純粹出於興趣自己睇哲學書 冇接受過任何哲學課程 所以唔敢睇原著有冇中文譯本? 我英文有啲差
我英文有啲差
 我英文有啲差
我英文有啲差諗過買kindle,想知你感覺兩者有咩分別
抱歉暫時找不到


請問有無世界金融史/貨幣史 推介?



我梗下唔係啦 都係門外漢嚟姐
但明康德要着手對付嘅問題同埋睇咗幾條講康德嘅片,識分先驗、後驗、分析、綜合同埋其他康德哲學名詞,我就入局睇原典
我仲睇緊好前嘅,transcendental aesthetics 嗰度姐,主要想知點解康德咁鬼勁,影響到後世所有西方哲學家,又創立咗german idealism,同埋私心想順住脈絡睇叔本華、佛家同尼采

但明康德要着手對付嘅問題同埋睇咗幾條講康德嘅片,識分先驗、後驗、分析、綜合同埋其他康德哲學名詞,我就入局睇原典
我仲睇緊好前嘅,transcendental aesthetics 嗰度姐,主要想知點解康德咁鬼勁,影響到後世所有西方哲學家,又創立咗german idealism,同埋私心想順住脈絡睇叔本華、佛家同尼采
呢本中學指定閱讀,我一收到就睇,結果用晒全日一口氣睇晒。描繪人物方面好寫實,故事寫到中國低下層嘅人點樣都擺脫唔到命運同時局嘅束縛,嗰種絕望感真係好sad。
最近書list:
文學:《笑忘書》
休閒:《築覺》、《藝術的故事》
漫畫:《女校之星》、《驀然回首》
文學:《笑忘書》
休閒:《築覺》、《藝術的故事》
漫畫:《女校之星》、《驀然回首》
想問個故事係邊個chapter

有買本書但一直隨心揀嚟睇


有買本書但一直隨心揀嚟睇
順住脈絡唔係應該睇下Hegel咩?
又係另一個大佬
牟中三話康德係通儒家
可以研究下
第一批判仲厚過字典
真係無心機睇
又係另一個大佬

牟中三話康德係通儒家
可以研究下
第一批判仲厚過字典
真係無心機睇

我會話Viktor Frankl 嘅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吧!
以我所知 其實分咗兩段路(粗略啲理解)嘅
Hegel就去咗absolute idealism
叔本華就延續康德嘅諗法 溝埋啲印度哲學
書就係讀吓讀吓沉迷當中就唔知時日過
唔經唔覺又讀咗本
又樂在其中 未嘗不可
Hegel就去咗absolute idealism
叔本華就延續康德嘅諗法 溝埋啲印度哲學
書就係讀吓讀吓沉迷當中就唔知時日過
唔經唔覺又讀咗本
又樂在其中 未嘗不可

Rule 1

個人認為呢本無論係文筆,結構(以頭兩篇去為第三篇埋伏筆)同對愛既描寫/reflection都係非常好,但都想提返你呢本始終唔係一本開心既書
希望你會鐘意

希望你會鐘意

揭左揭 黑格爾的倫理思想 幾有趣
再揭下其他:
Stace, W. T. (1924).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https://hk1lib.org/book/5274930/05a087
Taylor, C. (1975). Hegel.
https://hk1lib.org/book/3561552/955d57
Beiser, F. C. (2005). Hegel.
https://hk1lib.org/book/11235513/26750a
全靠大大推介Allen Wood打開大門
發現黑格爾幾有趣
我唔知自己再掘咩睇
大家有無咩相關書推介?
關於Hegel又得 唔關又得
再揭下其他:
Stace, W. T. (1924).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https://hk1lib.org/book/5274930/05a087
Taylor, C. (1975). Hegel.
https://hk1lib.org/book/3561552/955d57
Beiser, F. C. (2005). Hegel.
https://hk1lib.org/book/11235513/26750a
全靠大大推介Allen Wood打開大門
發現黑格爾幾有趣
我唔知自己再掘咩睇
大家有無咩相關書推介?
關於Hegel又得 唔關又得
有關黑格爾 skim時 覺有趣既 其中一個有關Kant既 我自己粗糙既理解:
Kant為理性劃限
Hegel認為理性就係有自我超越既傾向 會自然地靠近邏輯矛盾同悖論
Kant立二律背反 作為理性既界限
Hegel認為應該建立理論系統 將唔同既悖論 安置喺體系中適當既位置 就唔會再有矛盾
Kant為理性劃限
Hegel認為理性就係有自我超越既傾向 會自然地靠近邏輯矛盾同悖論
Kant立二律背反 作為理性既界限
Hegel認為應該建立理論系統 將唔同既悖論 安置喺體系中適當既位置 就唔會再有矛盾
Hegel 的話
聽聞Beiser嗰本易入口過Taylor
雖然我個人就最鼓勵人睇SEP嘅
聽聞Beiser嗰本易入口過Taylor
雖然我個人就最鼓勵人睇SEP嘅
見到唔少書友睇小說
我又忍唔住開咗本短短地嘅
係李琴峰嘅 《倒數五秒月牙》,相當之短,基本上一晚可以睇晒
有留意新聞的話,可能就聽過李琴峰呢個作家,因爲佢係臺灣人,日文係佢第二語言。然後佢用日文創作嘅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攞咗 芥川賞
訪問: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24-culture-taiwannese-writer-at-japan/
最初就係想睇呢本得獎作,但係未有中文版
噉唯有睇住有中文版嘅《倒數五秒月牙》先
呢本書有兩個故事,分別係「倒數五秒月牙」同埋「聖夜絲」
前者係講 //定居日本的臺灣女性上班族(亦是女同志身分)林妤梅,與一名至台灣教日文並與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女性淺羽實櫻,兩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林妤梅與淺羽實櫻是研究所時代的好友,相隔多年後在東京重逢,小說即是描述兩人重逢後共度的十個小時之內發生的事件,並由此引出彼此成長的背景,以及分別後的人生變化。//
後者就係講 臺灣女仔 孟月柔 同埋 日本嘅美術系大學生 瀨藤繪舞 之間嘅感情,發散討論到語言隔閡,加上同志感情嘅曖昧性,點樣令孟月柔喺段關係入面缺乏安全感。
睇到故事大綱都知
李琴峰嘅作品主要描寫女同志愛情
特色係故事劇情除咗明顯會講性傾向喺現實遇到嘅阻礙之外,更加會探討 跨語言(日文、中文、臺語)之間若即若離嘅關係、以及國族身份認同上兩邊不是人嘅疏離。
喺佢嘅筆下,兩者就好似 女同志嘅愛情一樣,同樣難以清晰明瞭噉言說,想講出口又無人明自己嘅第一身經驗
又例如呢段 對比華語系屬下唔同語言,再溝埋日文產生嘅化學反應,就相當精彩
我又忍唔住開咗本短短地嘅
係李琴峰嘅 《倒數五秒月牙》,相當之短,基本上一晚可以睇晒
有留意新聞的話,可能就聽過李琴峰呢個作家,因爲佢係臺灣人,日文係佢第二語言。然後佢用日文創作嘅小說《彼岸花盛開之島》攞咗 芥川賞

訪問: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24-culture-taiwannese-writer-at-japan/
最初就係想睇呢本得獎作,但係未有中文版
噉唯有睇住有中文版嘅《倒數五秒月牙》先

呢本書有兩個故事,分別係「倒數五秒月牙」同埋「聖夜絲」
前者係講 //定居日本的臺灣女性上班族(亦是女同志身分)林妤梅,與一名至台灣教日文並與台灣人結婚的日本女性淺羽實櫻,兩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林妤梅與淺羽實櫻是研究所時代的好友,相隔多年後在東京重逢,小說即是描述兩人重逢後共度的十個小時之內發生的事件,並由此引出彼此成長的背景,以及分別後的人生變化。//
後者就係講 臺灣女仔 孟月柔 同埋 日本嘅美術系大學生 瀨藤繪舞 之間嘅感情,發散討論到語言隔閡,加上同志感情嘅曖昧性,點樣令孟月柔喺段關係入面缺乏安全感。
睇到故事大綱都知
李琴峰嘅作品主要描寫女同志愛情

特色係故事劇情除咗明顯會講性傾向喺現實遇到嘅阻礙之外,更加會探討 跨語言(日文、中文、臺語)之間若即若離嘅關係、以及國族身份認同上兩邊不是人嘅疏離。
喺佢嘅筆下,兩者就好似 女同志嘅愛情一樣,同樣難以清晰明瞭噉言說,想講出口又無人明自己嘅第一身經驗

話語如絲,是人傳遞予人的意圖之絲。書面語言就像鐵絲般堅韌而確實,伸手便能碰觸捕捉,能夠慢慢體會其觸感;但口頭語言便如隨風飄搖擺動的蜘蛛之絲,明知眼前有一條絲線,卻怎麼也無法以雙手確實捕捉,沒有確切的觸感,有的僅是被細絲輕輕掠過的微弱焦慮感。連結我與繪舞的,便是那樣脆弱的絲線。若那絲線是以母語織成的,還能看得較為清晰,否則便彷彿視力減退一般,只能在模糊的視野裡尋找探索,試圖抓住那不可捉摸的絲線。我所能做的不過就是努力提高視力罷了,然而就像罹患近視便難以治癒一般,這樣的努力也終究有其極限。
。。。
觸摸彼此是用不著話語的。繪舞如是說。但人與人即便傾盡了話語都不見得能互相理解,沒有話語便更加不可能。說起來,若我是透過另一種語言的濾鏡來理解她所說的每一句話語,那麼她所欲傳遞的絲線與我所接收到的絲線,說不定便只是外表相似而已,其實內容全然不同。一思及此,我心中便產生一種難忍的焦慮。
又例如呢段 對比華語系屬下唔同語言,再溝埋日文產生嘅化學反應,就相當精彩

實櫻剛嫁過來時祖翁非常開心,因為他終於找到人陪他說日語了。實櫻祖翁剛好比實櫻大上一甲子,童年是日治時代,在學校學了日語。祖翁十幾歲時國民黨政權跑來台灣,祖翁的日本人身分連同說日語的權利便一併遭到剝奪。其後好長一段時間,祖翁都沒有機會使用日語。所以當他的孫子──實櫻丈夫──開始學日語時,他也開心得不得了;但要把日語學到能講能溝通,需要不少時間,過了不久祖翁也失望了,只得放棄和孫子說日語的念頭。
「お嬢さん、ようこそ。私は昭和の男だ(小姐,歡迎妳來,我是昭和的男人。)」
實櫻初次拜訪丈夫家中時,祖翁──當時還不是祖翁──如此對實櫻說道。
「私も昭和の女です。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也是昭和的女人,請多指教。)」
實櫻如此回應。穿越了漫長的時光甬道,昭和的首與尾終於得以在平成時代相見。
「恁攏毋知!日本人愛食ごぼう佮ふき啦!」
某個假日晚餐餐桌上,祖翁一邊以筷子夾著萵苣菜,一邊沒頭沒腦地說了這句話。一整家人面面相覷,沒有人能完全理解祖翁要表達什麼。實櫻聽不懂台語。其他人雖然聽得懂台語,明白祖翁在說「你們都不知道!日本人愛吃ごぼう和ふき啦!」,但最重要的「ごぼう(Gobou)」和「ふき(Fuki)」到底是什麼,他們則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ごぼう和ふき是什麼?」實櫻丈夫以中文詢問實櫻。
「ごぼう,是,『牛蒡』。」
實櫻把「ごぼう」翻成中文,但「ふき」的中文要怎麼說,實櫻也不知道。
那次對話就在沒有人完全理解意思的情況下不了了之,但在那之後祖翁仍頻繁地以日語對實櫻說:「ふき、身体に良い、だろう?(ふき,對身體好,對吧?)」彷彿意欲誇示自己對日本的理解程度。
祖翁被剝奪日語的時間實在太長,在穿越陰森漫長的時光甬道的期間,祖翁一個又一個地丟失了關於日語的記憶。雖然他拚了命想說日語,但記憶早已跟不上時光流逝。祖翁連要聽懂日語都頗為吃力,考慮到祖翁的日語理解能力已大不如昔,實櫻在傳達真正重要的事情時會盡量說中文,但即使如此祖翁仍固執地堅持要以日語回應,兩人因而往往無法順利進行溝通,對話也就常草草了事。
拚命抵抗語言的逆浪企圖泅泳向前的人不只有祖翁,實櫻也是如此。實櫻中文是在日本學的,其後又到中國留學,因此實櫻所講的中文偏向中國北方的發音,也就是普通話。普通話和台灣的國語擁有不同的特徵:四聲抑揚頓挫強烈,捲舌音清晰,前鼻音(n)和後鼻音(ng)也區分明顯。台灣的國語說話時的力道不需要那麼強。四聲相對平板,捲舌音也不太捲,無法區分前後兩種鼻音的人比比皆是。不只如此,台灣人說中文時總喜歡夾雜台語詞彙,讓剛來台灣的實櫻在聽力上吃盡了苦頭。且往往實櫻一開口講中文,便被嘲笑:「妳講的好像中國的中文。」
實櫻不想再被說自己講的是「中國的中文」,便決心接近台式發音,四聲和捲舌音、鼻音發音時都不要過於用力,盡量輕鬆。同時她仔細觀察周遭台灣人說話的語調以及用字遣詞,並且進行模仿。轉眼兩年經過,有次實櫻回日本時去拜訪大學時代的中文老師,結果中文老師笑著說:「妳的中文變成台灣的中文了呢。」實櫻不禁感到疑惑:自己講的中文難道不能是自己的東西,而非得是中國,或台灣的東西不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