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時份,我不知被甚麼驚動,短暫地醒來。矇矓間我看到Eunice坐了起,衣服還沒穿上,身子斜斜的背對著我。潔白的月光灑在她身上,貼伏在她的肌膚上流動,像水流過石礕。對街的霓虹卻也想佔一席地,毫不留情地染紅雪白無暇的月光,每當Eunice輕微的抖動時,紅和白就此消彼長地在她身上拉扯着。她本人卻似未察覺這場慘烈戰鬥似的,凝望着窗外不知甚麼地方。眼皮沉重不容我多看,又沉沉的睡去。
再次醒來時,魚肚白的陽光從窗外滲進來,卻沒有了Eunice的影子。直覺告訢我再也不會見到她了。我同時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和自我厭惡之中。並非因為對浚樂感到歉意,即使有那樣的成份,也是微乎其微。我也有想到這樣做算不算得上正確,怎麼說多少有些乘人之危,但正確與否對我來說,卻無甚麼分別。
如果人生是一個心電圖,要麼就是起伏不斷大起大落,要麼就是只有輕微起伏,甚至一條平線。我現在忍受的只是由高峰掉入低峪的痛苦,短暫上了橡皮艇,又被人掉回大海的感覺。僅此而己。
我由床上爭扎著起來,簡單梳洗後,離開這個混雜洗髮水、體味和廉價空氣清新劑的空間。我在7-11買了叉燒包和魚肉燒賣作早餐。店員問要不要熱奶茶時我果斷拒絕了,拿了一罐啤酒。
黃大仙Intern的所見所聞,及解籤要義初探
像我這樣尋找的人
287 回覆
93 Like
9 Dislike
十二、姜公又封相!?
人們求籤的內容可謂無奇不有。撇除有鬧事之人問黃大仙應不應該上廁所,還有不少是認真地問奇怪內容的。打開黃大仙靈籤Apps,就有幾個不知所云的項目,比如問天時到底是要問甚麼呢?難道打扙出兵之前才問的?實在不知所云。還有個較特別的,一個人在討論上找我解籤,問的居然是遺失。這是比較冷門的要求,畢竟在家裏不見了東西,大多數人會翻天覆地找尋不休,而非求神問卦。如果在別的地方不見,或者根本不知何時何地遺失,自知大海撈針,也不必驚動先師。找到找不到,大槪心裏有數,沒有甚麼懸而未決的地方要黃大仙決斷的。
這位朋友遺失的是一件手飾,好奇之下我請他把圖片傳給我看看,一看之下居然和我的手串幾乎一模一樣。我當下驚喜萬分。試想想,那條手串絕非貴重,誰又會為此大費周章呢?顯然是對他來說十分重要或有價值的。要是這樣,那會不會和通叔說的「六合六害續緣術」有關連呢?即使沒有,也大可向他打探手串的來歷。所以,我打算約他出來見面。
人們求籤的內容可謂無奇不有。撇除有鬧事之人問黃大仙應不應該上廁所,還有不少是認真地問奇怪內容的。打開黃大仙靈籤Apps,就有幾個不知所云的項目,比如問天時到底是要問甚麼呢?難道打扙出兵之前才問的?實在不知所云。還有個較特別的,一個人在討論上找我解籤,問的居然是遺失。這是比較冷門的要求,畢竟在家裏不見了東西,大多數人會翻天覆地找尋不休,而非求神問卦。如果在別的地方不見,或者根本不知何時何地遺失,自知大海撈針,也不必驚動先師。找到找不到,大槪心裏有數,沒有甚麼懸而未決的地方要黃大仙決斷的。
這位朋友遺失的是一件手飾,好奇之下我請他把圖片傳給我看看,一看之下居然和我的手串幾乎一模一樣。我當下驚喜萬分。試想想,那條手串絕非貴重,誰又會為此大費周章呢?顯然是對他來說十分重要或有價值的。要是這樣,那會不會和通叔說的「六合六害續緣術」有關連呢?即使沒有,也大可向他打探手串的來歷。所以,我打算約他出來見面。
新讀者留名

加速

又會咁樣無啦啦上左房都有

我先把自己的手串脫下來,放在窗檯上拍了一張照片。為了不被辨認出不盡相同的地方,我故意對焦不清,拍得模糊一點。他果然上當,忙問手串的來歷,我含糊其辭,只說是親戚偶然拾獲的,在何時何地則記不清了。我們約好在一家咖啡店見面,讓他看看實物。雖然不是騙財騙色,畢竟是刻意欺瞞,不免心虛,故約阿健同去,一來壯膽,二來他樣貌老實,對方疑心頓時減去大半。
應約那天我穿上鮮橙色上衫,墨綠色鴨咀帽,作為預先約好的相認記號。這是阿健提議的,說是他以前與人交易手板模型的經驗之談。他還說,若果穿得太平凡,恐有其他人穿著類同。但這個配拾也太過標奇立異,阿健一見到我也忍不住笑我像個食大茶飯的。我忍耐着旁人的目光大槪十五分鐘,目標人物終於出現。
應約那天我穿上鮮橙色上衫,墨綠色鴨咀帽,作為預先約好的相認記號。這是阿健提議的,說是他以前與人交易手板模型的經驗之談。他還說,若果穿得太平凡,恐有其他人穿著類同。但這個配拾也太過標奇立異,阿健一見到我也忍不住笑我像個食大茶飯的。我忍耐着旁人的目光大槪十五分鐘,目標人物終於出現。
是個五十來歲的阿姨,年紀身型都跟嫻姨差不多,但沒有嫻姨的濃妝厚粉。我打招時順手脫下忍無可忍的鴨咀帽,看時來像紳士在行禮。她大模大樣地把屁股塞進軟得像海綿的沙發,由少發下塌的速度,我真擔心她會整個人陷進海綿的旋渦裏。
「串珠呢?」她一坐下來就問,手心在桌子上一放,大有毒枭交易時的風範。
我連忙把手串交在她手裏,她反覆地端詳,又用拇指和食指手指逐顆珠捏著,最後失望的說:「真係好似,可惜唔係。」
說罷之後轉身就走。我早料定這串珠不能蒙混過關,便按設計好的對白說:「我親送咗呢條比我,佢仲有幾條。」
「仲有幾條,你唔係話佢執返黎架咩?」
想不到一下子被識穿,我忙圓謊說:「其實佢係個收藏家黎嘅,執到嗰個係佢個客,賣咗比佢姐。」
「呢啲嘢都有人收藏?」
「有架,咩都有人收藏架啦。我見過有人收集白膠漿潻。」說話的是阿健,想不到關鍵時刻他竟發揮作用。
「咁呀......」
「串珠呢?」她一坐下來就問,手心在桌子上一放,大有毒枭交易時的風範。
我連忙把手串交在她手裏,她反覆地端詳,又用拇指和食指手指逐顆珠捏著,最後失望的說:「真係好似,可惜唔係。」
說罷之後轉身就走。我早料定這串珠不能蒙混過關,便按設計好的對白說:「我親送咗呢條比我,佢仲有幾條。」
「仲有幾條,你唔係話佢執返黎架咩?」
想不到一下子被識穿,我忙圓謊說:「其實佢係個收藏家黎嘅,執到嗰個係佢個客,賣咗比佢姐。」
「呢啲嘢都有人收藏?」
「有架,咩都有人收藏架啦。我見過有人收集白膠漿潻。」說話的是阿健,想不到關鍵時刻他竟發揮作用。
「咁呀......」
每次入嚟都有文





看她猶豫之際,我忙改變話題,說:「係呢,條鏈對你好重要架?」
「老公送嘅。」
我心念一動,莫非......
「叫佢送過條囉,我睇呢啲珠應該唔難揾。」
「佢死咗啦。」
「Sorry,我唔係有心。」我連忙道歉。「咁你要唔要睇下我親戚嗰條?嘅然條手串對你咁重要。」
「咁呀.......都好嘅。你親間舖係邊?」
「黃大仙廟。」
「嗰度開舖?」她狐疑。
「唔係,不過佢有時係嗰度幫人解籤。」
她眼神閃過一絲驚疑。我心裏又是一動,莫非她是通叔前妻嗎?說所謂己經死去的丈夫就是通叔師弟?
「咁都係唔好啦,其實都唔見咗一段時間,好難揾得返。唔好浪費時間啦。」說著手搭在手袋上,就要起身。
我見大勢已去,當機立斷,打算直接跟她攤牌,問她認不認識通叔,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不如咁,我哋問多次黃大仙。」阿健突然插話,並掏出電話,上面正開着黃大仙靈籤。我想起上次Eunice的那支籤,黃大仙在某些時候總是很絕情的,尤其是這個住在電話裏的冒牌貨。這一把賭不過。
「老公送嘅。」
我心念一動,莫非......
「叫佢送過條囉,我睇呢啲珠應該唔難揾。」
「佢死咗啦。」
「Sorry,我唔係有心。」我連忙道歉。「咁你要唔要睇下我親戚嗰條?嘅然條手串對你咁重要。」
「咁呀.......都好嘅。你親間舖係邊?」
「黃大仙廟。」
「嗰度開舖?」她狐疑。
「唔係,不過佢有時係嗰度幫人解籤。」
她眼神閃過一絲驚疑。我心裏又是一動,莫非她是通叔前妻嗎?說所謂己經死去的丈夫就是通叔師弟?
「咁都係唔好啦,其實都唔見咗一段時間,好難揾得返。唔好浪費時間啦。」說著手搭在手袋上,就要起身。
我見大勢已去,當機立斷,打算直接跟她攤牌,問她認不認識通叔,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不如咁,我哋問多次黃大仙。」阿健突然插話,並掏出電話,上面正開着黃大仙靈籤。我想起上次Eunice的那支籤,黃大仙在某些時候總是很絕情的,尤其是這個住在電話裏的冒牌貨。這一把賭不過。
岩岩search先知真係有黃大仙求籤apps

好好睇 新人留名,不過睇到佢地搞野果part覺得有啲估唔到
新人留名,不過睇到佢地搞野果part覺得有啲估唔到
 新人留名,不過睇到佢地搞野果part覺得有啲估唔到
新人留名,不過睇到佢地搞野果part覺得有啲估唔到
我使個眼色想阻止阿健,但他視而不見,遞上手機,阿姨的指尖輕落在屏幕上,朱砂字寫上「靈」字的竹筒輕搖數下,然後命運塵埃落定。竟是第一籤。不必看籤文我也記得這是Eunice曾在茶樓求得的同一枝,上上籤。我心中暗叫僥倖。
「聽日三點,黃大仙正門見。」我一錘定音,不容她再三思。
「好彩姐,差啲瀨嘢。你咪咁衝動啦,黃大仙唔係次次都保祐架。」阿姨走後我責怪阿健。
阿健拿電話在我面前晃兩晃,又求一支籤, 又是第一籤。再求幾次,竟都是同一支。然後他打開執行中的程式總覽,我頓時明白,不禁失笑。
「黃大仙APP都開掛?小心天讉啊。」我笑說。
「係咪勁先,其他cheat engine就做唔到。」他自豪地說。
「係啊,快啲申請專利啦,求籤神器啊。」我說。
「聽日三點,黃大仙正門見。」我一錘定音,不容她再三思。
「好彩姐,差啲瀨嘢。你咪咁衝動啦,黃大仙唔係次次都保祐架。」阿姨走後我責怪阿健。
阿健拿電話在我面前晃兩晃,又求一支籤, 又是第一籤。再求幾次,竟都是同一支。然後他打開執行中的程式總覽,我頓時明白,不禁失笑。
「黃大仙APP都開掛?小心天讉啊。」我笑說。
「係咪勁先,其他cheat engine就做唔到。」他自豪地說。
「係啊,快啲申請專利啦,求籤神器啊。」我說。
呢個題材好有趣
竟然係同Eunice去左開房
想知Eunice仲會唔會出現
想知Eunice仲會唔會出現
偏在那天洛彤約我放工後見面,說有重要的事告知。兩點半,阿健whatsapp說就位。我從辦公室出來,今天不知是有甚麼活動,黃大仙祠內人山人海,好像過年一樣,為我們的計劃增潻了不明朗因素。我們約好等那位阿姨到達時,阿健陪着她,我去引通叔出來。
我們一直待到三點半,兩人都己經大汗淋漓,但還是不見人影。正當我以為她不會出現,一個人在我身後說:「你親戚呢?我無咩時間。」是那個阿姨,她戴着頂草帽,左顧右盼,像個朝庭欽犯。
「得,我宜家叫佢出黎。」
我穿過人群來到通叔攤檔,正如平常一樣,一個客人都沒有。我說有個重要的人要見他,半拉半騙的把他引出來。通叔身形肥腫,在人群中穿行不易,我一直擔心他頭上珍而重之幾條毛髮也會被人們手中的香火燒掉。
終於來到正門牌坊下,阿健正在低頭玩手機,那個阿姨卻不見了蹤影。
「人呢?」我忙問。
「吓,啱啱仲係度喎。」
「叫你睇住佢架啦。」
「sorry,女朋友揾我啊。」未成婚先成老婆奴。
我們一直待到三點半,兩人都己經大汗淋漓,但還是不見人影。正當我以為她不會出現,一個人在我身後說:「你親戚呢?我無咩時間。」是那個阿姨,她戴着頂草帽,左顧右盼,像個朝庭欽犯。
「得,我宜家叫佢出黎。」
我穿過人群來到通叔攤檔,正如平常一樣,一個客人都沒有。我說有個重要的人要見他,半拉半騙的把他引出來。通叔身形肥腫,在人群中穿行不易,我一直擔心他頭上珍而重之幾條毛髮也會被人們手中的香火燒掉。
終於來到正門牌坊下,阿健正在低頭玩手機,那個阿姨卻不見了蹤影。
「人呢?」我忙問。
「吓,啱啱仲係度喎。」
「叫你睇住佢架啦。」
「sorry,女朋友揾我啊。」未成婚先成老婆奴。
我四下張望,終於看到十二生肖像下,一頂草正在陽光下閃閃生輝。我吩咐通叔和阿健留在原地,追了過去。無數香火的飄煙織成一個個蜘蛛網,跟我糾纏不休。我只能緩慢前後,眯着眼睛,盯着浮在人海之上的那頂草帽,跟它之間的距離卻絲毫沒有縮短。
偏在這時電話響起來,Samsung特有的預設鈴聲,為四周的喧鬧加入強勁的節拍。我將手伸入褲袋掏手機,手臂上突然一陣刺痛,一把聲音大叫:「小心。」但為時已晚,那句小心為的不過推諉罪責,說明是我不小心,手臂才會被他的線香燙到。我顧不得痛繼續前行,手機響聲剛才停了一會,現在又響,我也不理會,邊行邊專心躲避香燭。
不知不覺間,草帽已經領着我繞了一圈,跟當日和洛彤一起走的路線幾乎一樣。然而,我們之間還是隔着不變的距離,我走快點它也跟着加速,我遇到阻礙它又故意等著我似的,並不拉開距離。最後草帽拐個彎,由出口鑽出去了。我連忙跟上,卻哪裏有蹤影? 門外面並無固定的路,人潮四下分散,要再追蹤怕是千難萬難。我有點失落嘆了口氣,手串的線索中斷了,通叔也跟前妻緣慳一面。
偏在這時電話響起來,Samsung特有的預設鈴聲,為四周的喧鬧加入強勁的節拍。我將手伸入褲袋掏手機,手臂上突然一陣刺痛,一把聲音大叫:「小心。」但為時已晚,那句小心為的不過推諉罪責,說明是我不小心,手臂才會被他的線香燙到。我顧不得痛繼續前行,手機響聲剛才停了一會,現在又響,我也不理會,邊行邊專心躲避香燭。
不知不覺間,草帽已經領着我繞了一圈,跟當日和洛彤一起走的路線幾乎一樣。然而,我們之間還是隔着不變的距離,我走快點它也跟着加速,我遇到阻礙它又故意等著我似的,並不拉開距離。最後草帽拐個彎,由出口鑽出去了。我連忙跟上,卻哪裏有蹤影? 門外面並無固定的路,人潮四下分散,要再追蹤怕是千難萬難。我有點失落嘆了口氣,手串的線索中斷了,通叔也跟前妻緣慳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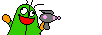 推
推這時我眼角的餘光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洛彤。身旁還有個高個子體型壯健的男孩。他們兩人都戴着那條手串。我的心像被甚麼錘了一下似的。不知怎地,我竟害怕被他們看見,急忙別過臉去。
這時手機又響了,煩人的鈴聲現在卻讓我心懷感激。
「喂。」是阿健的聲音。「通叔心臟病發暈咗。」
這時手機又響了,煩人的鈴聲現在卻讓我心懷感激。
「喂。」是阿健的聲音。「通叔心臟病發暈咗。」
十三、 第100籤 唐明皇擊鼓摧花
我憂心忡忡地前踏上往聯合醫院的路上。通叔若有不測,我良心如何過得去?引他去見那位可能是他前妻的阿姨,雖然也是為了他著想,但大部份也為了我個人的好奇心。結果他誰也見不着,若為此送了命,實在不值。我思量着,他不過跟着我走了一段不足三分鍾的路.......也不是算走得很快罷?不足以引發心臟病吧?但我又留他在陽光下曝曬......有多久呢?我在Google輸入「太陽」、「心藏病」,頭一則是關於多曬太陽可以促進心臟健康,我心頭一寛。但再往下看有一則新聞,「曬太陽時間過長可誘發心臟病」,內文說「大部份人以為冬天是心臟病的高危病發時間,卻忽略夏天猛烈的陽光也是引致心臟病的元兇之一。長時間在日光下曝曬,缺乏補充,可引致缺水,並發心臟病,須小心提防.......」
我憂心忡忡地前踏上往聯合醫院的路上。通叔若有不測,我良心如何過得去?引他去見那位可能是他前妻的阿姨,雖然也是為了他著想,但大部份也為了我個人的好奇心。結果他誰也見不着,若為此送了命,實在不值。我思量着,他不過跟着我走了一段不足三分鍾的路.......也不是算走得很快罷?不足以引發心臟病吧?但我又留他在陽光下曝曬......有多久呢?我在Google輸入「太陽」、「心藏病」,頭一則是關於多曬太陽可以促進心臟健康,我心頭一寛。但再往下看有一則新聞,「曬太陽時間過長可誘發心臟病」,內文說「大部份人以為冬天是心臟病的高危病發時間,卻忽略夏天猛烈的陽光也是引致心臟病的元兇之一。長時間在日光下曝曬,缺乏補充,可引致缺水,並發心臟病,須小心提防.......」
胡思亂想間,小巴扺達聯合醫院。我致電阿健問了通叔的病房號碼。看看樓層指示牌,那應該屬於老人病房,並非深切治療部,一時三刻應該沒生命危險。但我要到達病房卻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因為電梯大堂探病的人龍足足折疉了七疉。如果病人處於彌留狀態,親友由大堂到達病床之時,那人也早已走過孟婆橋了。
花了半小時,我終於成功上樓。阿健守在通叔病房門口看手機。
「佢點呀?」我憂心忡忡地問。
「冇......中暑姐,醫生話觀察一晚就可以出院。」
「吓,又話心藏病?」
「咁我見佢撳住個心口,又暈咗,咪以為.......你知啦,佢又咁肥......」
「頂。」
花了半小時,我終於成功上樓。阿健守在通叔病房門口看手機。
「佢點呀?」我憂心忡忡地問。
「冇......中暑姐,醫生話觀察一晚就可以出院。」
「吓,又話心藏病?」
「咁我見佢撳住個心口,又暈咗,咪以為.......你知啦,佢又咁肥......」
「頂。」
lm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