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來瑞典沒有貓》在北歐遇見一個天真爛漫地尋死的女生
西樓月如鈎
1001 回覆
554 Like
25 Dislike
留言已經好好

留名等文

等文
放工啦想快啲有文睇

放工啦想快啲有文睇
屌live 左
冇嘅!

樓主晚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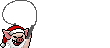 個故起身未
個故起身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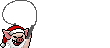 個故起身未
個故起身未
瑞典的舊城區(Gamla stan)是遊客旺區,基本上每個去瑞典的人也會到此一遊,原因是所有特色的地標和博物館也集中在這裏,包括諾貝爾博物館和王宮,還有不少手信店舖。
說到瑞典的咖啡,它的特色就是⋯⋯其實沒什麼特色,反正我不是咖啡愛好者,對我而言根本沒什麼損失,而且我只會喝齋啡,奶茶也是,我覺得加了什麼添加料,如糖這些會破壞味道的原汁原味。
在中午,喝一口咖啡也是不錯的選擇。
牙膏不斷在我身旁整理自己的衣服和頭髮,左照鏡左照鏡,好像新郎等待新娘一樣。
「你知佢係女嚟㗎可?」我問。
「我知呀。所以第一印象好緊要嘛。」
「女你都啱?」
「你份人個思想點解咁污穢?朋友唔得嘅?」他抱怨道。
「男朋友定女朋友。」
「無你咁好氣。」
「同埋人哋都未必嚟。」我說。
是的,其實她沒有說明一定會來。
當早上我把小黑的相片寄給她,並說其實瑞典是有貓時,她只是這樣回我。
「好可愛,可惜牠不是貓。」
有時我真的覺得她不是常人一般的腦袋。
「那牠是什麼?」
「你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啦。」
「我說牠是貓,那牠是貓。」
「可惜牠不是。」
「妳不是講,我說牠是什麼,牠就是什麼?」
「但你心裏面根本不是覺得牠是貓。」
真敗給她,連我的想法也猜透?
「妳今天有空嗎?」
「想約我?」
「我們會去舊城區,妳會來一起?」
「我們?」
「我和我的朋友。」
她只是回覆:「看情況。」
我把咖啡店的位置報給她,所以她來不來我根本不知道。
牙膏說,這是考驗她是否對我仍然有興趣。
「呢個係第一次見面後嘅成績表。」他說。
等待的中途,決定走出咖啡店遊逛一下,在岸邊有鳥飛過和落地休憩,一個一個像排隊一樣,而且會跟途人玩耍,動物與人的關係比較和洽,這是香港難以看見。



說到瑞典的咖啡,它的特色就是⋯⋯其實沒什麼特色,反正我不是咖啡愛好者,對我而言根本沒什麼損失,而且我只會喝齋啡,奶茶也是,我覺得加了什麼添加料,如糖這些會破壞味道的原汁原味。
在中午,喝一口咖啡也是不錯的選擇。
牙膏不斷在我身旁整理自己的衣服和頭髮,左照鏡左照鏡,好像新郎等待新娘一樣。
「你知佢係女嚟㗎可?」我問。
「我知呀。所以第一印象好緊要嘛。」
「女你都啱?」
「你份人個思想點解咁污穢?朋友唔得嘅?」他抱怨道。
「男朋友定女朋友。」
「無你咁好氣。」
「同埋人哋都未必嚟。」我說。
是的,其實她沒有說明一定會來。
當早上我把小黑的相片寄給她,並說其實瑞典是有貓時,她只是這樣回我。
「好可愛,可惜牠不是貓。」
有時我真的覺得她不是常人一般的腦袋。
「那牠是什麼?」
「你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啦。」
「我說牠是貓,那牠是貓。」
「可惜牠不是。」
「妳不是講,我說牠是什麼,牠就是什麼?」
「但你心裏面根本不是覺得牠是貓。」
真敗給她,連我的想法也猜透?
「妳今天有空嗎?」
「想約我?」
「我們會去舊城區,妳會來一起?」
「我們?」
「我和我的朋友。」
她只是回覆:「看情況。」
我把咖啡店的位置報給她,所以她來不來我根本不知道。
牙膏說,這是考驗她是否對我仍然有興趣。
「呢個係第一次見面後嘅成績表。」他說。
等待的中途,決定走出咖啡店遊逛一下,在岸邊有鳥飛過和落地休憩,一個一個像排隊一樣,而且會跟途人玩耍,動物與人的關係比較和洽,這是香港難以看見。



啱啱醒咗,有心

斷估會出現
唔出現應該冇咁多野寫

唔出現應該冇咁多野寫

唔出現
——————————全文完——————————
——————————全文完——————————
唔出現會係
《原來瑞典沒有女》在北歐同牙膏hehe的故事


《原來瑞典沒有女》在北歐同牙膏hehe的故事



咪成日踢爆主線

good ending



Gamla Stan正呀 最鍾意中古建築,可惜諾貝爾冇得放香港人,得How dare you
最鍾意中古建築,可惜諾貝爾冇得放香港人,得How dare you
 最鍾意中古建築,可惜諾貝爾冇得放香港人,得How dare you
最鍾意中古建築,可惜諾貝爾冇得放香港人,得How dare you
have la
聽你講係由大阪番黎香港程機到追左你個大阪故


 sad到...
sad到...
不過好寫實 愛情總係要有遺憾先係悽美
btw呢個出快少少得唔得



 sad到...
sad到...不過好寫實 愛情總係要有遺憾先係悽美
btw呢個出快少少得唔得

Lm
多謝晒,好聽話啵
多人睇咪快啲

多人睇咪快啲

Hello景行

多謝
遲早識到啦

遲早識到啦

遲啲就有

無啦

午後的陽光在照射到水面,波光粼粼,微風輕掃岸邊,吹起點點思緒。
周采蘋會否來,這真是一個好問題,我也想知道。
再回到咖啡廳,已經過了一個小時多,仍未見人,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
「嗯⋯⋯」牙膏說:「我又唔介意等嘅。」
嘴巴是這樣講,但我也不想讓他受等待的罪。
「算啦,我哋走啦,可能第一次見面我真係太悶。」我說。
越想越覺得上次跟周采蘋見面,自己的表現簡直是一塌糊塗,又難怪別人不願意再來。
「唔使問下佢先?」牙膏說。
「唔使啦。」我說:「唔想好似逼人,我哋周圍行下。」
舊城區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大教堂,美侖美奐,聞說瑞典舊城有一段長時間都暗不見光(其實冬季就是),教堂就仿如光明照亮那時的人心。
對於教堂美不美,我心裏實在沒有概念,只會分覺得舒服不舒服(而我覺得這間不舒服)但對返教會十多年的牙膏來說,應該就比較易分。而我連教堂是否天主教或新教也分不清,也是他告訴我天主教的教會佈局大概會是怎樣。


他雖然離開教會,但我覺得他的心仍然在教會,只不過被逼着離開。
我們在教堂內,望着十字架,我實在想不明白,於是問:「其實教會由聖人組成咩?」
「唔係呀,教會成日都會堅稱自己由罪人組成。」
「咁點解你要走?」
「因為佢哋覺得呢種係罪,違反自然,所以我一定要改。」
「咁其他人係咪已經改晒佢哋嘅罪?」
「基督信仰係講每個人都係一個無力嘅罪人,不能自救,一生都係會咁,所以要靠十字架。」
「咁既然係咁,一個罪人點解要咁有力指責另一個罪人?」
「唉你唔明㗎啦。」
「我唔明,但我為你覺得痛心啫。」
我是不明白。
大自然也有動物會同性戀,什麼是違反自然,我實在不明白。有什麼比宣稱愛的組織把一個人掃出教會更違反自然?
這條路,真的好難走。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們就離開這座教堂。

此時,就收到她的訊息。
「你還在咖啡廳?」
周采蘋會否來,這真是一個好問題,我也想知道。
再回到咖啡廳,已經過了一個小時多,仍未見人,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
「嗯⋯⋯」牙膏說:「我又唔介意等嘅。」
嘴巴是這樣講,但我也不想讓他受等待的罪。
「算啦,我哋走啦,可能第一次見面我真係太悶。」我說。
越想越覺得上次跟周采蘋見面,自己的表現簡直是一塌糊塗,又難怪別人不願意再來。
「唔使問下佢先?」牙膏說。
「唔使啦。」我說:「唔想好似逼人,我哋周圍行下。」
舊城區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大教堂,美侖美奐,聞說瑞典舊城有一段長時間都暗不見光(其實冬季就是),教堂就仿如光明照亮那時的人心。
對於教堂美不美,我心裏實在沒有概念,只會分覺得舒服不舒服(而我覺得這間不舒服)但對返教會十多年的牙膏來說,應該就比較易分。而我連教堂是否天主教或新教也分不清,也是他告訴我天主教的教會佈局大概會是怎樣。


他雖然離開教會,但我覺得他的心仍然在教會,只不過被逼着離開。
我們在教堂內,望着十字架,我實在想不明白,於是問:「其實教會由聖人組成咩?」
「唔係呀,教會成日都會堅稱自己由罪人組成。」
「咁點解你要走?」
「因為佢哋覺得呢種係罪,違反自然,所以我一定要改。」
「咁其他人係咪已經改晒佢哋嘅罪?」
「基督信仰係講每個人都係一個無力嘅罪人,不能自救,一生都係會咁,所以要靠十字架。」
「咁既然係咁,一個罪人點解要咁有力指責另一個罪人?」
「唉你唔明㗎啦。」
「我唔明,但我為你覺得痛心啫。」
我是不明白。
大自然也有動物會同性戀,什麼是違反自然,我實在不明白。有什麼比宣稱愛的組織把一個人掃出教會更違反自然?
這條路,真的好難走。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們就離開這座教堂。

此時,就收到她的訊息。
「你還在咖啡廳?」
聽日會唔會開到新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