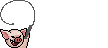讀者指南:
1. 你宜家即將閱讀嘅係一個奇幻長故,全文微甜擦邊,SM,暴力,殘忍,復仇反Cap,目前至少有五十五集稿,寫緊第二篇章,只要你睇到邊正皮到邊,我就會一直寫,直到無正皮就唔會係呢個Post更文。
2. 由第二篇章完結後起,每次篇章完結都會有核爆甜內容,追落去先可以Lam到重甜嘅果實。

3. 主角係一個被人性暴力過嘅男仔,雖然會敘事交代啲仆街點對佢,但係本書任何角色16歲之前,我僅限敘事交代,唔會花筆墨去營造煽情氣氛。
4. 你其實可以去Penana睇到同一個故事去到五十五集,但作者宜家睇正皮更文,邊度有正皮就會係邊度更落去,你一直正皮可能後期仲會追得遠過Penana。
作者狀態:
1. 作者知道奇幻好小眾,合理期望,總之有正皮,俾我知你有睇就會更文,最多寫緊,唔會棄。
2. 宜家心理好自律,呢個post入面除咗更文同回覆讀者,唔會為咗鳩推叫春。
村惡‧【一】斷奶、喪父、秘銀師
自從年半前父親在夏天完結之夜離開了母親與尼祿,一個邪惡的命題就開始像鬼一樣攪擾著他的腦袋:
人的共存即是暴力,別無他態。
對於一個未足十一歲的少年來說,擁有這種極端而缺乏彈性的信念是極其罕見的,尼祿之所以如此深信,絕無經歷過那種哲人在博覽群書之後從腦內結晶得出思想精華的神聖過程,與此徹底地反調著,這是一個僅可閱字的俗人在親身體驗過後從身體流淌出血與膿液的污穢總結。
他首次遭受暴力侵害的時候,卻是遠在父親離開之前的事,那時候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正在目擊父母的交配,那位一直與他親密緊貼,餵哺他奶水的母親,在他的面前呈現著赤裸的面貌與另一個個體互相衝突耗損,幼體生命的原始本能凌駕了他未發育成熟的思考神經,他感覺自己遭受到拋棄與惡待。
父親用如同刺刀的那話兒刺穿著母親的陰戶,因為母親俯撐床邊的姿勢,她的乳房呈現了下垂而動亂的陌生狀態,完全不同於平時在餵奶或與尼祿共浴時因為身體垂直而安放靜止的美麗狀態。
「插死你這個賤人!殺死你!」
父親明知在床上假睡的尼祿正透過眼縫看到一切,而父親卻選擇了冷眼與尼祿對視,一邊講著上述殘忍的話。
「殺死我!不殺死我你就是垃圾!殺死我!!嗚!」
母親狠毒卻悽慘的呻吟聲令他想起以前那隻因為被其他小孩綁住石頭而在河水中窒息致死的小狗哀號,這時父親從後用巨大的手掌一手扯鬆了母親在早上梳洗整齊的髮髻,父親的另一隻手則托在母親的喉嚨之前將其捏到變形,在死亡的邊際,母親的兩腿一陣抽搐發軟,身體一度死寂在床邊,尼祿嚇壞了,他以為父親殺死了母親,也覺得他身體入面有一不可名狀的部分一併被殺死了。
由這天起,他就不敢再啜食母親的奶頭,母親見他斷奶,那就將他從床舖趕去屋子另一邊的毛氈上睡,怕黑的尼祿每晚顫抖至深夜,連風吹草動都響若雷聲,他以為窗外飛過的甲蟲是飛天的魔鬼,又以為野狗的吠叫是在密謀將他連骨吃掉。
日子過去,童年的恐懼與憤怒早已被時間的細砂埋葬進內心深處,九歲的尼祿忘記了當初與母親分床的細節及原因,他敬愛著自己的父母親,不快樂但平淡地發育成長著。
只是那在人與人斷續狀態下產生的暴力陰影,早趁這些年間在砂土墳丘之上悄悄冒芽蔓延,到他父親離去的時候,暴力的開花結果也就像秋梨般汁水豐盛了。
尼祿記得在父親離開的那一晚,他們收留了一個外地來的男人,男人的右腳正包裹在污血布帶之中,如果要走路,男人便要像一個斷腳的人一樣借助開叉的結實樹枝代替右腳,他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身份,但父母一致認為他是從戰場上逃跑出來的秘銀師,安全起見,父母拒絕了男人留宿一晚的要求,但當男人的瞳仁閃過了黃銅色的光,父母便回心轉意了,父親讓出了自己的床,然後連行李都不收拾就離開家門自此遠去。
這晚上男人把母親壓在床邊,用他如同刺刀的那話兒刺穿著母親的陰戶。
「殺死我!不殺死我你就是垃圾!殺死我!!嗚!」
無力抵抗的母親,說出了契合著尼祿凋淡記憶中的同一句話。
這夜他一晚醒著,也喚醒了那棵將陽光徹底遮蔽的暴力之樹。
Penana: https://www.penana.com/story/61795/%E8%A3%A1%E5%A5%87%E5%B9%BB-%E7%A7%98%E9%8A%80-%E9%8B%BC%E9%90%B5-%E5%9C%93%E7%9F%B3/issu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