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w新聞台】DSE2025年中文科筆試今日開考,DSE中文科近4.9萬名考生報考,DSE考生已經完成閱讀及寫作兩卷。本台整理DSE中學文憑試今年卷二寫作題目一覽:
DSE中文卷二甲部實用文:
DSE中文寫作卷,自2024年改制,考生須寫實用文和命題作文,一共兩篇,兩文分別佔試卷分數3成與7成。
實用文考核「大熱」體裁──演講辭,議題關於寵物棄養與領養,考生須以中學義工服務團的學生代表名義,寫一篇早會演講辭,說明義工團舉行寵物領養計劃的意義,游說學生支持。
實用文只設一題,必考,內文不得多於550字,超出字數或扣分。
DSE中文卷二乙部命題寫作:
命題寫作3選1,內文不得少於650字。
‧藏在泥土中的寶物
‧為不完美添色彩
‧「行事要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
「要踏出舒適圈,才可以突破能力的界限。」
談談對以上兩個觀點的看法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599139
DSE中文|命題寫作:藏在泥土的寶物、為不完美添色彩
6.16HK
141 回覆
8 Like
29 Dislike
好的,這是一個關於核戰後世界,主角與機器人尋找適合耕種土地的故事,約1200字:
藏在泥土下的寶藏
核戰後的荒蕪大地,天空永遠灰濛濛的,刺鼻的輻射塵埃瀰漫在空氣中,陽光像被一層厚重的紗布遮住,透不出絲毫暖意。大部分的土地都受到了嚴重的輻射污染,無法耕種,人類的生存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主角李維,一個在廢墟中長大的年輕人,他擁有一雙堅毅的眼睛,和一顆永不放棄的心。他的夥伴,是名為Bob的古老機器人,Bob雖然外表斑駁,但內部的運算核心卻異常強大,擁有豐富的土壤分析數據和地圖資料。
「Bob,今天我們往哪個方向走?」李維背著沉重的行囊,望著一望無際的荒涼大地。
「根據地圖顯示,北方有一片區域,輻射指數相對較低,或許存在適合耕種的土壤。」Bob用機械式的聲音回答,全息地圖在他眼前展開,標示著他們目前的位置和目標區域。
兩人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旅程。荒蕪的城市廢墟,傾頹的高樓大廈,鏽跡斑斑的汽車殘骸,這些曾經繁華的象徵,如今都成了死亡的見證。他們穿越了無數個被輻射侵蝕的區域,忍受著惡劣的氣候和稀缺的食物。
一天,他們來到了一片被厚重雲層籠罩的區域,這裡的空氣異常潮濕,地面上長著一些奇特的綠色植物。
「這裡的輻射指數很低,土壤濕度也適合耕種。」Bob分析著土壤樣本,「但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才能確定土壤的肥沃程度。」
李維和Bob開始挖掘,他們挖得很深,終於在地下發現了一層黑色的土壤,土壤散發著淡淡的泥土芬芳,這是核戰後極為罕見的景象。
「這土壤富含養分,可以耕種!」李維興奮地說,他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泥土,就像捧著珍貴的寶藏。
他們開始在這片土地上播種,種子是他們從廢墟中找到的,是核戰前遺留下來的珍貴遺產。他們每天都細心照料著這些幼苗,期待著它們能茁壯成長。
幾個月後,奇蹟發生了,幼苗突破了地表,長出了嫩綠的葉子,在這片荒蕪的大地上,綠色顯得格外耀眼。
「我們成功了!」李維激動地擁抱著Bob,「我們找到了藏在泥土下的寶藏!」
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小小的農場,種植了各種蔬菜和水果,這些食物不僅能讓他們生存下去,也給了他們希望。
消息傳開了,其他倖存者紛紛來到這裡,他們學習李維和Bob的耕種方法,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園。
荒蕪的大地,因為李維和Bob的努力,重新煥發了生機。他們找到了藏在泥土下的寶藏,那不僅是適合耕種的土地,更是人類在絕望中重生的希望。
藏在泥土下的寶藏
核戰後的荒蕪大地,天空永遠灰濛濛的,刺鼻的輻射塵埃瀰漫在空氣中,陽光像被一層厚重的紗布遮住,透不出絲毫暖意。大部分的土地都受到了嚴重的輻射污染,無法耕種,人類的生存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主角李維,一個在廢墟中長大的年輕人,他擁有一雙堅毅的眼睛,和一顆永不放棄的心。他的夥伴,是名為Bob的古老機器人,Bob雖然外表斑駁,但內部的運算核心卻異常強大,擁有豐富的土壤分析數據和地圖資料。
「Bob,今天我們往哪個方向走?」李維背著沉重的行囊,望著一望無際的荒涼大地。
「根據地圖顯示,北方有一片區域,輻射指數相對較低,或許存在適合耕種的土壤。」Bob用機械式的聲音回答,全息地圖在他眼前展開,標示著他們目前的位置和目標區域。
兩人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旅程。荒蕪的城市廢墟,傾頹的高樓大廈,鏽跡斑斑的汽車殘骸,這些曾經繁華的象徵,如今都成了死亡的見證。他們穿越了無數個被輻射侵蝕的區域,忍受著惡劣的氣候和稀缺的食物。
一天,他們來到了一片被厚重雲層籠罩的區域,這裡的空氣異常潮濕,地面上長著一些奇特的綠色植物。
「這裡的輻射指數很低,土壤濕度也適合耕種。」Bob分析著土壤樣本,「但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才能確定土壤的肥沃程度。」
李維和Bob開始挖掘,他們挖得很深,終於在地下發現了一層黑色的土壤,土壤散發著淡淡的泥土芬芳,這是核戰後極為罕見的景象。
「這土壤富含養分,可以耕種!」李維興奮地說,他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泥土,就像捧著珍貴的寶藏。
他們開始在這片土地上播種,種子是他們從廢墟中找到的,是核戰前遺留下來的珍貴遺產。他們每天都細心照料著這些幼苗,期待著它們能茁壯成長。
幾個月後,奇蹟發生了,幼苗突破了地表,長出了嫩綠的葉子,在這片荒蕪的大地上,綠色顯得格外耀眼。
「我們成功了!」李維激動地擁抱著Bob,「我們找到了藏在泥土下的寶藏!」
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小小的農場,種植了各種蔬菜和水果,這些食物不僅能讓他們生存下去,也給了他們希望。
消息傳開了,其他倖存者紛紛來到這裡,他們學習李維和Bob的耕種方法,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園。
荒蕪的大地,因為李維和Bob的努力,重新煥發了生機。他們找到了藏在泥土下的寶藏,那不僅是適合耕種的土地,更是人類在絕望中重生的希望。
「行事要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這句話如同暮鼓晨鐘,提醒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應當審慎評估自身的能力,避免因過度逞強而招致失敗。它蘊含著一種務實的智慧,告誡我們要尊重客觀規律,避免不切實際的幻想。然而,與此同時,「要踏出舒適圈,才可以突破能力的界限。」這句話則像一聲嘹亮的號角,鼓舞我們勇於挑戰自我,敢於探索未知的領域,唯有如此,才能不斷拓展人生的邊界,實現個人的成長與飛躍。這兩個觀點看似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但細細品味,卻能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係,在不同的情境下,各自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行事要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無疑是經驗的總結,是無數次失敗教訓的凝練。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事情的成功都建立在充分的準備和對自身能力的清晰認知之上。例如,一個體力有限的人,若勉強去搬運超出負荷的重物,輕則腰酸背痛,重則可能造成身體損傷。一個學識尚淺的學生,若勉強去挑戰超出自己理解範圍的學術難題,往往會感到挫敗和迷茫,最終可能一無所獲。在商業領域,一個資金不足、經驗匱乏的企業,若勉強去擴張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業務,很容易陷入財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這些例子都印證了「量力而為」的重要性。它提醒我們,在行動之前要進行周全的考量,評估自身的資源、能力和經驗,選擇與之相匹配的目標和方法。避免盲目自信,更要杜絕意氣用事,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失敗的風險,穩紮穩打地前行。這種謹慎的態度,是保護自己,也是對目標負責的體現。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現狀,永遠固守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麼個人的能力和潛能就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發揮和提升。「溫水煮青蛙」的故事警示我們,過度的舒適和安逸會使人喪失進取心和應變能力,最終被時代所淘汰。「要踏出舒適圈,才可以突破能力的界限。」正是對這種保守思想的有力反駁。舒適圈雖然令人感到安全和自在,但也像一個無形的牢籠,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和發展。只有勇敢地邁出這一步,去嘗試新的事物,挑戰未知的領域,我們才能發現自己潛在的能力,學習新的技能,拓展新的思維方式。就像一個初學游泳的人,只有敢於離開岸邊,投入水中,才能學會如何在水中自由馳騁。一個害怕失敗的發明家,只有敢於不斷嘗試和實驗,才能最終創造出劃時代的成果。每一次對舒適圈的挑戰,都是一次成長的機會,都是一次能力邊界的拓展。正是這種不斷挑戰自我的精神,推動著個人和社會的不斷進步。
那麼,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觀點,是否就水火不容呢?我認為並非如此。它們更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不同的階段和情境下,需要我們做出明智的權衡和選擇。真正的智慧,或許就在於如何在「量力而為」的基礎上,勇敢地「踏出舒適圈」。
首先,「量力而為」並非意味著永遠停留在原地,而是要對自身的能力有一個客觀的評估,並以此為基礎制定合理的目標。這個目標可以略高於自身現有的能力,但不能過於懸殊,以至於完全無法企及。其次,「踏出舒適圈」也並非盲目冒險,而是要有一定的準備和規劃。在挑戰新領域之前,需要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了解可能的風險和挑戰,並制定應對方案。這就好比登山,我們需要評估自己的體能,選擇適合的路線,準備必要的裝備,而不是毫無準備地去攀登險峰。
因此,我認為對這兩個觀點的理解應該是辯證統一的。「行事要量力而為」是基礎和前提,它保證了我們行動的穩健性,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要踏出舒適圈」則是動力和方向,它驅使我們不斷挑戰自我,實現能力的提升。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我們可能需要側重不同的方面。在初入社會、經驗不足時,或許更應謹慎行事,量力而為;當具備一定的基礎和經驗後,則應勇於挑戰舒適圈,尋求更大的突破。
總而言之,「行事要量力而為」提醒我們要腳踏實地,避免盲目冒進;「要踏出舒適圈」則激勵我們要勇於挑戰,不斷突破自我。這兩者並非絕對對立,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只有在清晰認識自身能力的基礎上,審慎地選擇挑戰的目標和方式,我們才能在穩健前行的同時,不斷拓展能力的邊界,最終實現個人的價值和夢想。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領悟。
「行事要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無疑是經驗的總結,是無數次失敗教訓的凝練。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事情的成功都建立在充分的準備和對自身能力的清晰認知之上。例如,一個體力有限的人,若勉強去搬運超出負荷的重物,輕則腰酸背痛,重則可能造成身體損傷。一個學識尚淺的學生,若勉強去挑戰超出自己理解範圍的學術難題,往往會感到挫敗和迷茫,最終可能一無所獲。在商業領域,一個資金不足、經驗匱乏的企業,若勉強去擴張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業務,很容易陷入財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這些例子都印證了「量力而為」的重要性。它提醒我們,在行動之前要進行周全的考量,評估自身的資源、能力和經驗,選擇與之相匹配的目標和方法。避免盲目自信,更要杜絕意氣用事,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失敗的風險,穩紮穩打地前行。這種謹慎的態度,是保護自己,也是對目標負責的體現。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現狀,永遠固守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麼個人的能力和潛能就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發揮和提升。「溫水煮青蛙」的故事警示我們,過度的舒適和安逸會使人喪失進取心和應變能力,最終被時代所淘汰。「要踏出舒適圈,才可以突破能力的界限。」正是對這種保守思想的有力反駁。舒適圈雖然令人感到安全和自在,但也像一個無形的牢籠,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和發展。只有勇敢地邁出這一步,去嘗試新的事物,挑戰未知的領域,我們才能發現自己潛在的能力,學習新的技能,拓展新的思維方式。就像一個初學游泳的人,只有敢於離開岸邊,投入水中,才能學會如何在水中自由馳騁。一個害怕失敗的發明家,只有敢於不斷嘗試和實驗,才能最終創造出劃時代的成果。每一次對舒適圈的挑戰,都是一次成長的機會,都是一次能力邊界的拓展。正是這種不斷挑戰自我的精神,推動著個人和社會的不斷進步。
那麼,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觀點,是否就水火不容呢?我認為並非如此。它們更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不同的階段和情境下,需要我們做出明智的權衡和選擇。真正的智慧,或許就在於如何在「量力而為」的基礎上,勇敢地「踏出舒適圈」。
首先,「量力而為」並非意味著永遠停留在原地,而是要對自身的能力有一個客觀的評估,並以此為基礎制定合理的目標。這個目標可以略高於自身現有的能力,但不能過於懸殊,以至於完全無法企及。其次,「踏出舒適圈」也並非盲目冒險,而是要有一定的準備和規劃。在挑戰新領域之前,需要學習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了解可能的風險和挑戰,並制定應對方案。這就好比登山,我們需要評估自己的體能,選擇適合的路線,準備必要的裝備,而不是毫無準備地去攀登險峰。
因此,我認為對這兩個觀點的理解應該是辯證統一的。「行事要量力而為」是基礎和前提,它保證了我們行動的穩健性,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要踏出舒適圈」則是動力和方向,它驅使我們不斷挑戰自我,實現能力的提升。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我們可能需要側重不同的方面。在初入社會、經驗不足時,或許更應謹慎行事,量力而為;當具備一定的基礎和經驗後,則應勇於挑戰舒適圈,尋求更大的突破。
總而言之,「行事要量力而為」提醒我們要腳踏實地,避免盲目冒進;「要踏出舒適圈」則激勵我們要勇於挑戰,不斷突破自我。這兩者並非絕對對立,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只有在清晰認識自身能力的基礎上,審慎地選擇挑戰的目標和方式,我們才能在穩健前行的同時,不斷拓展能力的邊界,最終實現個人的價值和夢想。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領悟。
 AI真係玩哂
AI真係玩哂所以話咗
未來公開試必修科
係應該轉為考工科、砌機械人同遙控機械呢啲新時代手動嘅工作
你要寫一篇靚文
AI兩三秒已經搞掂
大學嘅文科已經冇存在嘅必要
生活如同一個巨大的園圃,表面上看去或許平淡無奇,甚至偶有塵埃與蕪雜,但正如深諳園藝之人所知,肥沃的泥土之下,往往孕育著令人驚喜的種子與潛藏的根脈。這不禁使人聯想到,真正的價值是否也常常深藏於我們所忽略的平凡之中,如同那靜靜躺臥在泥土裡的寶物,等待著有心人的發掘?
泥土的意象是多重的。它可以是我們周遭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環境。在日復一日的行程中,我們容易變得麻木,忽略了身邊潛藏的美好與機會。鄰里間的溫情問候,街角咖啡店的醇厚香氣,公園裡盛開的不知名野花,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如同藏在泥土中的寶物,蘊含著生活的真諦與幸福的源泉。只是我們往往腳步匆匆,眼神迷離,未能駐足欣賞,用心感受。如同辛勤的農夫,只有深耕細作,才能從看似貧瘠的土地中孕育出豐碩的果實。生活亦然,需要我們放慢腳步,細心觀察,才能在平凡的泥土中發現那些被忽略的寶藏。
泥土亦可比喻為艱難困苦的逆境。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挫折、失敗、磨難如同厚重的泥土,將我們緊緊包裹,令人感到窒息和絕望。然而,正如經歷寒冬的泥土才能孕育出春天的生機,逆境往往也是磨練意志、積累經驗的沃土。那些在困境中不屈不撓、奮力抗爭的人們,如同在泥土中頑強生長的種子,最終破土而出,綻放出生命的光彩。他們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從磨難中錘煉品格,那些曾經的傷痛與艱辛,都轉化為他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正如蚌殼中的沙粒,經過長久的磨礪,最終蛻變成璀璨的珍珠。因此,面對逆境,我們不應抱怨泥土的沉重,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挑戰和考驗,相信其中必將蘊藏著成長與蛻變的寶物。
更深一層地理解,「泥土」還可以指代我們內在的潛能與德行,這些往往被外在的浮華所掩蓋。現代社會過於注重外在的物質追求和表面的光鮮亮麗,而忽略了內在的修養和精神的富足。如同被塵土蒙蔽的古董,我們內心深處的善良、智慧、堅韌、創造力等寶貴品質,常常被忙碌的生活和功利的慾望所掩蓋。只有透過不斷地反省、學習和修煉,拂去心靈的塵埃,才能真正認識和發掘這些內在的寶藏。一個擁有高尚品格的人,即使身處逆境,也能散發出令人敬佩的光芒;一個擁有真才實學的人,即使一時不被賞識,也終將在合適的時機展現其價值。真正的寶物,往往深藏於內心深處的泥土之中,需要我們用心去耕耘和呵護。
此外,「泥土」亦可引申為那些被時間長河所掩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智慧。在現代文明的快速發展中,許多古老的技藝、傳統的習俗、樸素的哲理,如同被泥土掩蓋的文物,逐漸被人們所遺忘。然而,這些看似陳舊的事物,往往蘊含著前人世代積累的智慧和經驗,是我們文化Identity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發掘和傳承這些「藏在泥土中的寶物」,不僅能夠豐富我們的文化底蘊,也能為我們應對當代社會的挑戰提供有益的啟示。例如,傳統的手工藝中蘊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細節的精益求精;古老的哲學思想中蘊含著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深刻思考。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珍視和傳承的寶貴財富。
總而言之,「藏在泥土中的寶物」是一個富有哲理的命題,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價值往往並非顯而易見,而是需要我們以細膩的觀察、堅韌的毅力、深刻的洞察力去發掘。無論是生活中的美好細節,逆境中的成長契機,內在的潛能德行,還是被遺忘的歷史文化,都如同深藏於泥土中的寶物,等待著我們去用心發現,並使其綻放出屬於它們的璀璨光芒。只有學會彎下腰,撥開泥土,我們才能真正領略到這個世界所蘊藏的豐富與美好。
泥土的意象是多重的。它可以是我們周遭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環境。在日復一日的行程中,我們容易變得麻木,忽略了身邊潛藏的美好與機會。鄰里間的溫情問候,街角咖啡店的醇厚香氣,公園裡盛開的不知名野花,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如同藏在泥土中的寶物,蘊含著生活的真諦與幸福的源泉。只是我們往往腳步匆匆,眼神迷離,未能駐足欣賞,用心感受。如同辛勤的農夫,只有深耕細作,才能從看似貧瘠的土地中孕育出豐碩的果實。生活亦然,需要我們放慢腳步,細心觀察,才能在平凡的泥土中發現那些被忽略的寶藏。
泥土亦可比喻為艱難困苦的逆境。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挫折、失敗、磨難如同厚重的泥土,將我們緊緊包裹,令人感到窒息和絕望。然而,正如經歷寒冬的泥土才能孕育出春天的生機,逆境往往也是磨練意志、積累經驗的沃土。那些在困境中不屈不撓、奮力抗爭的人們,如同在泥土中頑強生長的種子,最終破土而出,綻放出生命的光彩。他們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從磨難中錘煉品格,那些曾經的傷痛與艱辛,都轉化為他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正如蚌殼中的沙粒,經過長久的磨礪,最終蛻變成璀璨的珍珠。因此,面對逆境,我們不應抱怨泥土的沉重,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挑戰和考驗,相信其中必將蘊藏著成長與蛻變的寶物。
更深一層地理解,「泥土」還可以指代我們內在的潛能與德行,這些往往被外在的浮華所掩蓋。現代社會過於注重外在的物質追求和表面的光鮮亮麗,而忽略了內在的修養和精神的富足。如同被塵土蒙蔽的古董,我們內心深處的善良、智慧、堅韌、創造力等寶貴品質,常常被忙碌的生活和功利的慾望所掩蓋。只有透過不斷地反省、學習和修煉,拂去心靈的塵埃,才能真正認識和發掘這些內在的寶藏。一個擁有高尚品格的人,即使身處逆境,也能散發出令人敬佩的光芒;一個擁有真才實學的人,即使一時不被賞識,也終將在合適的時機展現其價值。真正的寶物,往往深藏於內心深處的泥土之中,需要我們用心去耕耘和呵護。
此外,「泥土」亦可引申為那些被時間長河所掩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智慧。在現代文明的快速發展中,許多古老的技藝、傳統的習俗、樸素的哲理,如同被泥土掩蓋的文物,逐漸被人們所遺忘。然而,這些看似陳舊的事物,往往蘊含著前人世代積累的智慧和經驗,是我們文化Identity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發掘和傳承這些「藏在泥土中的寶物」,不僅能夠豐富我們的文化底蘊,也能為我們應對當代社會的挑戰提供有益的啟示。例如,傳統的手工藝中蘊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細節的精益求精;古老的哲學思想中蘊含著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深刻思考。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珍視和傳承的寶貴財富。
總而言之,「藏在泥土中的寶物」是一個富有哲理的命題,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價值往往並非顯而易見,而是需要我們以細膩的觀察、堅韌的毅力、深刻的洞察力去發掘。無論是生活中的美好細節,逆境中的成長契機,內在的潛能德行,還是被遺忘的歷史文化,都如同深藏於泥土中的寶物,等待著我們去用心發現,並使其綻放出屬於它們的璀璨光芒。只有學會彎下腰,撥開泥土,我們才能真正領略到這個世界所蘊藏的豐富與美好。
人生畫布,底色並非全然潔白無瑕,細看之下,總會發現或深或淺的墨點,或粗或細的裂痕。這些被視為「不完美」的印記,彷彿是造物主不經意間留下的痕跡,常令我們感到缺憾,甚至試圖極力抹除。然而,倘若換一個角度審視,或許正是這些看似不完美的元素,如同畫布上待著色的留白,賦予了我們揮灑創意、展現獨特的機會,讓我們得以「為不完美添色彩」,繪製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風景。
個人的成長歷程中,所謂的「不完美」往往以缺點、不足、遺憾等形式呈現。或許是天生的短板,例如不擅長運動,或是性格上的弱點,例如容易焦慮。面對這些與理想自我有所差距的地方,我們或許會感到沮喪,甚至產生自卑的情緒。然而,正是對這些不完美的認知與接納,驅使我們不斷學習與改進。一個不擅長言辭的人,可能會更用心傾聽,並在文字表達上下功夫;一個容易焦慮的人,可能會學習放鬆技巧,培養更穩定的情緒。這些努力,就像為原本單調的底色塗抹上不同的色彩,使我們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元。與其一味地否定和掩蓋不完美,不如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起點,透過後天的努力和智慧,為其增添屬於自己的光彩。
生活本身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完美」。計劃趕不上變化,突如其來的意外,無法彌補的遺憾,這些都是構成生活肌理的一部分。我們無法預知所有的風雨,也無法避免所有的失落。然而,面對這些生活中的不完美,我們並非只能選擇黯然神傷。如同修復一件破損的瓷器,即使裂痕無法完全消失,但透過精巧的工藝,卻可以賦予其新的美感與價值。面對生活的缺憾,我們可以選擇積極應對,從中學習,轉化負面情緒,尋找新的希望與方向。一次失敗的經歷,可以成為下一次成功的基石;一段逝去的感情,可以讓我們更加珍惜當下所擁有的。正是這些經歷,如同畫筆下的色彩,層層疊加,繪就出我們獨特的人生故事。
進一步而言,「為不完美添色彩」也可以延伸至對社會和世界的觀察。社會上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例如貧富差距、環境污染、文化衝突等等。這些可以被視為社會的「不完美」。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並非只能袖手旁觀,抱怨世界的糟糕。每一個個體的微小努力,如同為黑白照片添上一抹色彩,都能為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貢獻力量。關注弱勢群體,參與環保行動,促進文化交流,這些都是在為不完美的社會增添希望和美好的色彩。正是無數人的積極參與和不懈努力,才能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甚至在藝術的領域,「不完美」也常常是靈感的來源。「殘缺的美」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欣賞。一件經歷歲月洗禮的古物,其斑駁的痕跡反而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一首略帶瑕疵的歌曲,其真摯的情感可能更能打動人心。藝術家常常從生活的不完美中汲取靈感,透過獨特的視角和表現手法,將其轉化為令人驚嘆的藝術作品。如同日本的「侘寂」美學,欣賞事物的不完美、無常和簡樸,從中發現獨特的美感。這啟示我們,不完美並非全然是負面的,它也可以是一種獨特的魅力,等待我們去發現和欣賞。
總而言之,「為不完美添色彩」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創造性的實踐。它鼓勵我們接納自身和生活中的不完美,並以積極的行動、智慧和創意去彌補、改善、轉化,甚至欣賞這些不完美。如同畫家在不完美的畫布上揮灑色彩,我們也能在不完美的人生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彩與意義。正是這些色彩的點綴,使得我們的人生畫卷更加生動、豐富、獨特,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
個人的成長歷程中,所謂的「不完美」往往以缺點、不足、遺憾等形式呈現。或許是天生的短板,例如不擅長運動,或是性格上的弱點,例如容易焦慮。面對這些與理想自我有所差距的地方,我們或許會感到沮喪,甚至產生自卑的情緒。然而,正是對這些不完美的認知與接納,驅使我們不斷學習與改進。一個不擅長言辭的人,可能會更用心傾聽,並在文字表達上下功夫;一個容易焦慮的人,可能會學習放鬆技巧,培養更穩定的情緒。這些努力,就像為原本單調的底色塗抹上不同的色彩,使我們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元。與其一味地否定和掩蓋不完美,不如將其視為一種獨特的起點,透過後天的努力和智慧,為其增添屬於自己的光彩。
生活本身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完美」。計劃趕不上變化,突如其來的意外,無法彌補的遺憾,這些都是構成生活肌理的一部分。我們無法預知所有的風雨,也無法避免所有的失落。然而,面對這些生活中的不完美,我們並非只能選擇黯然神傷。如同修復一件破損的瓷器,即使裂痕無法完全消失,但透過精巧的工藝,卻可以賦予其新的美感與價值。面對生活的缺憾,我們可以選擇積極應對,從中學習,轉化負面情緒,尋找新的希望與方向。一次失敗的經歷,可以成為下一次成功的基石;一段逝去的感情,可以讓我們更加珍惜當下所擁有的。正是這些經歷,如同畫筆下的色彩,層層疊加,繪就出我們獨特的人生故事。
進一步而言,「為不完美添色彩」也可以延伸至對社會和世界的觀察。社會上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例如貧富差距、環境污染、文化衝突等等。這些可以被視為社會的「不完美」。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並非只能袖手旁觀,抱怨世界的糟糕。每一個個體的微小努力,如同為黑白照片添上一抹色彩,都能為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貢獻力量。關注弱勢群體,參與環保行動,促進文化交流,這些都是在為不完美的社會增添希望和美好的色彩。正是無數人的積極參與和不懈努力,才能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甚至在藝術的領域,「不完美」也常常是靈感的來源。「殘缺的美」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欣賞。一件經歷歲月洗禮的古物,其斑駁的痕跡反而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一首略帶瑕疵的歌曲,其真摯的情感可能更能打動人心。藝術家常常從生活的不完美中汲取靈感,透過獨特的視角和表現手法,將其轉化為令人驚嘆的藝術作品。如同日本的「侘寂」美學,欣賞事物的不完美、無常和簡樸,從中發現獨特的美感。這啟示我們,不完美並非全然是負面的,它也可以是一種獨特的魅力,等待我們去發現和欣賞。
總而言之,「為不完美添色彩」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創造性的實踐。它鼓勵我們接納自身和生活中的不完美,並以積極的行動、智慧和創意去彌補、改善、轉化,甚至欣賞這些不完美。如同畫家在不完美的畫布上揮灑色彩,我們也能在不完美的人生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彩與意義。正是這些色彩的點綴,使得我們的人生畫卷更加生動、豐富、獨特,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
那最初的白,曾是我對世界最純粹的期許,像一方無垠的雪地,渴望著被人類腳印所賦予意義。然而,歲月如不經意的潑墨,總會在潔白之上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那是挫敗的黯淡,是遺憾的暈染,是無可避免的缺憾,如同畫布上那些起初令我不安的斑駁。
我曾凝視著那些不完美,如同審視著鏡中不夠精緻的容顏,心底泛起一絲難以言喻的失落。彷彿一首期待完美的樂章,不小心滑落的音符,在寂靜中顯得格外突兀。我試圖用力的擦拭,想要將那些痕跡抹去,讓一切重歸最初的純粹。指尖摩挲,卻只留下更深的印記,提醒著我,有些事物一旦發生,便如同樹木的年輪,成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漸漸地,我開始學會放慢腳步,如同欣賞一幅歷經滄桑的古畫。那些曾經被我視為瑕疵的痕跡,細細看來,竟也蘊含著獨特的紋理。那一道彎曲的裂痕,像極了人生蜿蜒的曲徑,記載著迷途的徬徨與最終的柳暗花明;那一塊暈開的墨跡,彷彿是淚水浸潤過的痕跡,沉澱著過往的傷痛,卻也映照出雨後彩虹的絢爛。
我開始明白,生命的本質或許就是一場不斷填色的旅程。那最初的白,只是提供了一張空白的畫布,而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點滴,卻是上帝不小心灑下的顏料,等待著我們以自己的心意去暈染、勾勒。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任由那些斑駁在孤寂中蔓延;也可以拾起手中的畫筆,蘸取名為勇氣、名為智慧、名為愛意的色彩,小心翼翼地,為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添上屬於自己的光芒。
那曾經讓我感到羞赧的缺點,如今,我試著用勤奮的汗水去浸潤,讓它綻放出努力的光澤。那曾經讓我耿耿於懷的遺憾,如今,我試著用理解的柔光去撫平,讓它沉澱為智慧的珍珠。我不再苛求完美,因為我知道,真正的美麗,往往蘊藏在那些獨特的印記之中。如同夜空中的星辰,正是因為有了陰影的映襯,才更顯得璀璨奪目。
為不完美添色彩,並非是掩蓋或粉飾,而是一種坦然的接納,一種積極的轉化,一種用獨特的方式去詮釋生命的藝術。每一筆色彩的落下,都是一次與自我的和解,都是一次對生命的熱愛。當我用心為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塗抹上屬於我的色彩時,我看到的是一幅更加豐富、更加真實、也更加動人的畫卷。那不再是單調的白,而是經歷過風雨,依然充滿生機的斑斕世界。
於是,我漸漸愛上了這幅並不完美的畫布,愛上了那些獨特的色彩,因為我知道,這才是生命最真實的模樣,這才是屬於我,獨一無二的光彩。讓那些曾經的缺憾,都開出名為堅強的花朵;讓那些未盡的期許,都繪成未來可期的畫卷。為不完美添色彩,用愛與勇氣,將生命的留白,都填滿屬於自己的詩意與芬芳。
我曾凝視著那些不完美,如同審視著鏡中不夠精緻的容顏,心底泛起一絲難以言喻的失落。彷彿一首期待完美的樂章,不小心滑落的音符,在寂靜中顯得格外突兀。我試圖用力的擦拭,想要將那些痕跡抹去,讓一切重歸最初的純粹。指尖摩挲,卻只留下更深的印記,提醒著我,有些事物一旦發生,便如同樹木的年輪,成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漸漸地,我開始學會放慢腳步,如同欣賞一幅歷經滄桑的古畫。那些曾經被我視為瑕疵的痕跡,細細看來,竟也蘊含著獨特的紋理。那一道彎曲的裂痕,像極了人生蜿蜒的曲徑,記載著迷途的徬徨與最終的柳暗花明;那一塊暈開的墨跡,彷彿是淚水浸潤過的痕跡,沉澱著過往的傷痛,卻也映照出雨後彩虹的絢爛。
我開始明白,生命的本質或許就是一場不斷填色的旅程。那最初的白,只是提供了一張空白的畫布,而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點滴,卻是上帝不小心灑下的顏料,等待著我們以自己的心意去暈染、勾勒。我們可以選擇視而不見,任由那些斑駁在孤寂中蔓延;也可以拾起手中的畫筆,蘸取名為勇氣、名為智慧、名為愛意的色彩,小心翼翼地,為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添上屬於自己的光芒。
那曾經讓我感到羞赧的缺點,如今,我試著用勤奮的汗水去浸潤,讓它綻放出努力的光澤。那曾經讓我耿耿於懷的遺憾,如今,我試著用理解的柔光去撫平,讓它沉澱為智慧的珍珠。我不再苛求完美,因為我知道,真正的美麗,往往蘊藏在那些獨特的印記之中。如同夜空中的星辰,正是因為有了陰影的映襯,才更顯得璀璨奪目。
為不完美添色彩,並非是掩蓋或粉飾,而是一種坦然的接納,一種積極的轉化,一種用獨特的方式去詮釋生命的藝術。每一筆色彩的落下,都是一次與自我的和解,都是一次對生命的熱愛。當我用心為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塗抹上屬於我的色彩時,我看到的是一幅更加豐富、更加真實、也更加動人的畫卷。那不再是單調的白,而是經歷過風雨,依然充滿生機的斑斕世界。
於是,我漸漸愛上了這幅並不完美的畫布,愛上了那些獨特的色彩,因為我知道,這才是生命最真實的模樣,這才是屬於我,獨一無二的光彩。讓那些曾經的缺憾,都開出名為堅強的花朵;讓那些未盡的期許,都繪成未來可期的畫卷。為不完美添色彩,用愛與勇氣,將生命的留白,都填滿屬於自己的詩意與芬芳。
 作家level
作家level老實講而家公開試仲唔轉模式
下一代人一定會被淘汰
明明全個世界都去緊第四次工業革命
AI機械人時代
香港個學制仲未強制學生讀電腦同工科
真係想自毀下一代?

呢篇好空
上面#7 轉抒情文mode 仲勁
上面#7 轉抒情文mode 仲勁
玩完
利申: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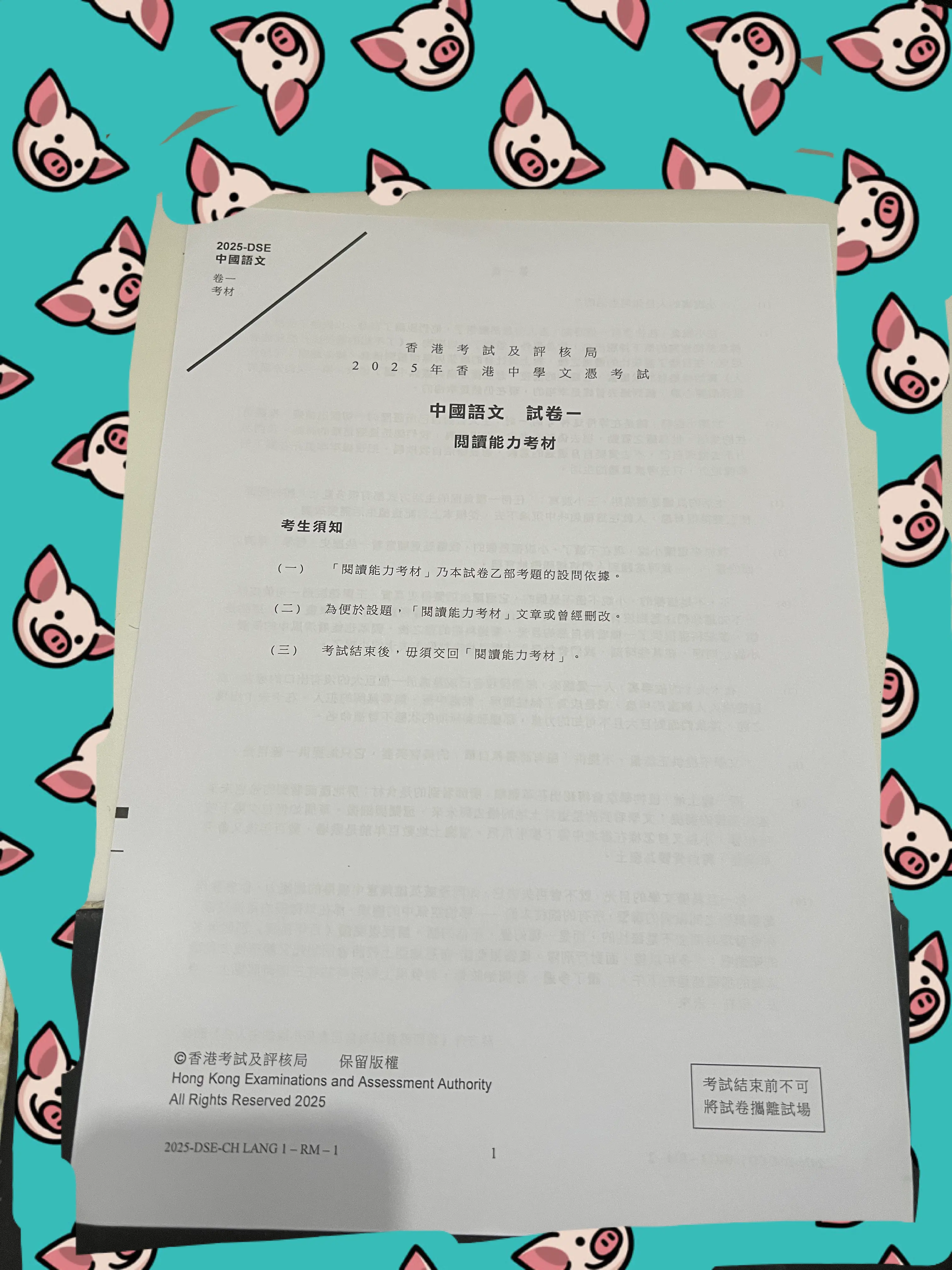

利申: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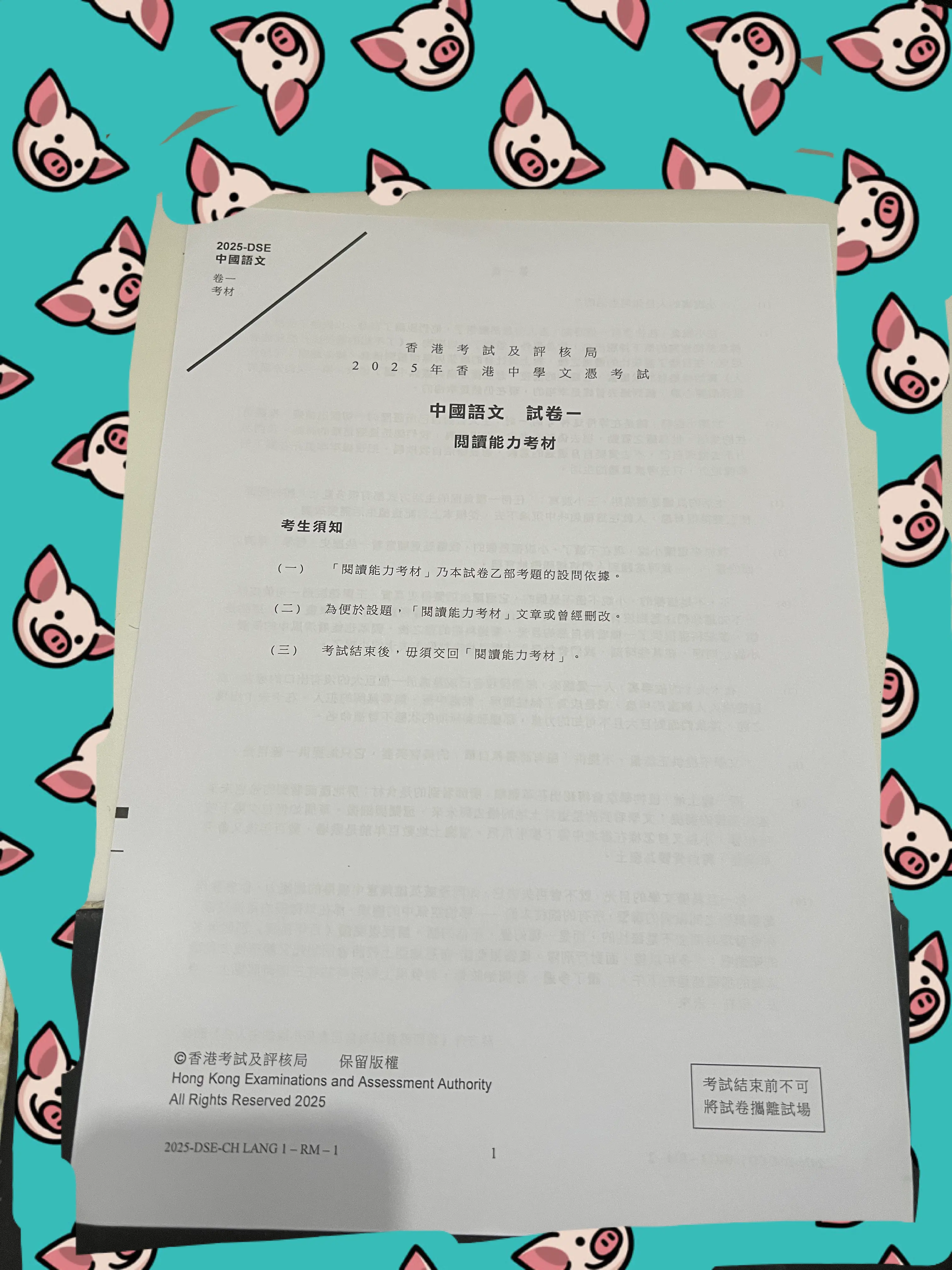
唔影埋考生編號點信你

 黐撚線
黐撚線勁到屈哂機
不如試吓叫佢用村上春樹個tone再寫一篇?

咖啡的蒸汽氤氳而上,模糊了窗外四月的倫敦雨絲。雨點敲打著老舊的窗框,發出細微而有節奏的聲響,像是誰在輕輕哼唱一首不知名的爵士樂。我啜了一口微苦的咖啡,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只缺了一角的舊馬克杯上。缺口邊緣有些許歲月的磨損,觸摸起來帶著一絲粗糙的溫暖。它並不完美,甚至可以說有點殘缺,但它卻是我每天早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或許,人生也是這樣一種存在吧。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像精密的瑞士錶那般準確無誤,也沒有誰的生活能像精心修剪的花園般完美無瑕。總會有些許的錯位,一些無法彌補的遺憾,像是歌詞裡突然跑調的音符,或者記憶深處一塊無法拼湊完整的碎片。那些不完美,如同散落在時間長河裡的鵝卵石,形狀各異,觸感冰涼,卻真實地構成了我們走過的路。
我常常在深夜裡,獨自一人坐在書桌前,聽著那些老舊的唱片。那些略帶雜音的旋律,那些歌手略微沙啞的嗓音,並非全然的完美,卻彷彿擁有一種直抵內心的力量。它們像是歲月留下的刻痕,記錄著當時的情緒,當時的光影。正是那些微小的瑕疵,讓音樂變得更加真實,更加貼近生活原本的模樣。
為不完美添色彩,並非是要刻意去修飾那些缺憾,讓一切看起來毫無瑕疵。那樣做,或許會失去一些真實的質感,如同過度曝光的照片,反而失去了細節和層次。真正的添色,或許更像是在接受那些既定的事實之後,以一種溫柔而富於想像力的方式,去重新看待它們。
就像那只缺角的馬克杯,它的不完美並沒有妨礙我用它來盛裝溫暖的咖啡。相反,那個缺口反而成為了它的標誌,一個獨一無二的印記,提醒著我它經歷過的一些故事,一些我無從知曉的日常。我小心翼翼地握著它,感受著那份不完美的真實。
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像爵士樂手即興演奏那樣,在既有的旋律和節奏中,加入一些意想不到的音符,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略帶跑調的即興段落。那些看似不和諧的音符,有時卻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讓整首樂曲充滿了獨特的生命力。
倫敦的雨依舊在下,淅淅瀝瀝,彷彿永不停歇。我望著窗外被雨水洗刷過的街道,那些濕漉漉的石板路,那些撐著雨傘匆匆而過的行人,每個人都像是在各自的故事裡前行,而每個故事,想必都或多或少地摻雜著一些不完美。但正是這些不完美,才讓每個故事都變得獨一無二,如同雨後天空那抹不期而遇的彩虹,為原本灰濛濛的世界,添上了一抹意想不到的色彩。而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就是在那份不完美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色彩,然後,繼續前行。
或許,人生也是這樣一種存在吧。並非所有的事情都像精密的瑞士錶那般準確無誤,也沒有誰的生活能像精心修剪的花園般完美無瑕。總會有些許的錯位,一些無法彌補的遺憾,像是歌詞裡突然跑調的音符,或者記憶深處一塊無法拼湊完整的碎片。那些不完美,如同散落在時間長河裡的鵝卵石,形狀各異,觸感冰涼,卻真實地構成了我們走過的路。
我常常在深夜裡,獨自一人坐在書桌前,聽著那些老舊的唱片。那些略帶雜音的旋律,那些歌手略微沙啞的嗓音,並非全然的完美,卻彷彿擁有一種直抵內心的力量。它們像是歲月留下的刻痕,記錄著當時的情緒,當時的光影。正是那些微小的瑕疵,讓音樂變得更加真實,更加貼近生活原本的模樣。
為不完美添色彩,並非是要刻意去修飾那些缺憾,讓一切看起來毫無瑕疵。那樣做,或許會失去一些真實的質感,如同過度曝光的照片,反而失去了細節和層次。真正的添色,或許更像是在接受那些既定的事實之後,以一種溫柔而富於想像力的方式,去重新看待它們。
就像那只缺角的馬克杯,它的不完美並沒有妨礙我用它來盛裝溫暖的咖啡。相反,那個缺口反而成為了它的標誌,一個獨一無二的印記,提醒著我它經歷過的一些故事,一些我無從知曉的日常。我小心翼翼地握著它,感受著那份不完美的真實。
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像爵士樂手即興演奏那樣,在既有的旋律和節奏中,加入一些意想不到的音符,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略帶跑調的即興段落。那些看似不和諧的音符,有時卻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讓整首樂曲充滿了獨特的生命力。
倫敦的雨依舊在下,淅淅瀝瀝,彷彿永不停歇。我望著窗外被雨水洗刷過的街道,那些濕漉漉的石板路,那些撐著雨傘匆匆而過的行人,每個人都像是在各自的故事裡前行,而每個故事,想必都或多或少地摻雜著一些不完美。但正是這些不完美,才讓每個故事都變得獨一無二,如同雨後天空那抹不期而遇的彩虹,為原本灰濛濛的世界,添上了一抹意想不到的色彩。而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就是在那份不完美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色彩,然後,繼續前行。
 嘩黐咗線
嘩黐咗線諾貝爾文學獎level
各大學文科正式收皮

你叫蕭源同林溢欣用三個鐘去寫
都未必寫到呢個level嘅7成

上面班ai撚做乜鳩?
作文就係考學生有冇表達能力同思辯能力,你用ai gen到幾千字但出到黎講野成個弱智咁有春用?
上threads睇都見到唔少00 10後寫野真係連基本邏輯都冇
 口試根本唔應該取消
口試根本唔應該取消

作文就係考學生有冇表達能力同思辯能力,你用ai gen到幾千字但出到黎講野成個弱智咁有春用?
上threads睇都見到唔少00 10後寫野真係連基本邏輯都冇
 口試根本唔應該取消
口試根本唔應該取消古龍 tone:-
江湖上最令人動容的傳說,永遠都與寶物有關。
寶物藏於何處?或在高山峻嶺之巔,或在大海深處幽冥。然而,最不可思議的寶藏,竟深藏於泥土之間。
楚寒山腳下的小鎮,夕陽如血,煙雲繚繞。這裡不曾出過名動天下的大俠,卻流傳著一個江湖傳說。一位老者,行將就木之際,曾言:「此地藏寶,得之者富甲天下。」
從此,小鎮便不再寧靜。
無數俠客奔赴此地,江湖好漢、名門世家、甚至市井小民,都為這一句話瘋狂。有人掘地三尺,有人深入溪澗,但尋得的,盡是黃沙碎石,終究不見寶藏的蹤影。
時日久遠,人們漸漸失望離去,楚寒山下又重歸寧靜。
但有一人未走。
他姓方,單名一個正字,江湖無名,樣貌平凡,偏偏多了一雙清亮如星辰的眼睛。他不動鏟、不動刀,只在田間漫步,眼神卻專注異常。
他看著泥土,看著稻穗,看著風吹過草地時的輕柔波紋。他凝視之處,彷彿世界都在他眼前悄然變幻。
終有一天,他蹲下身來,撿起一塊沾滿泥土的石子,拂去灰塵,嘴角微微上揚。
「找到了。」他的聲音輕柔如風。
村民們圍來看熱鬧,見他手裡不過是一塊毫不起眼的泥石,頓時哄堂大笑。
「這便是你苦尋多年的寶藏?」有人嘲諷。
方正卻微笑不語,只將石子放入懷中,轉身離去。他的步伐從容,如攜天下珍寶。
幾年後,江湖忽然傳來一個名號——方正。
他用一塊看似平凡的泥石,鑄成了一柄無雙利器,那兵刃名震天下,竟可斷金裂玉。寶劍出鞘之日,無數人恍然大悟,原來當日被世人所棄如泥土的石子,竟是世間難求的玄鐵。
而楚寒山腳下的泥土,因為蘊藏著珍貴的玄鐵礦脈,也自此成為江湖中人必爭之地。
許多人重返小鎮,意欲重尋當日的機緣,但卻再無一人能如方正般尋得真正的寶物。
人們終於明白,寶物或許人人可得,但只有那些真正看透泥土價值的人,才能從最不起眼的所在,發掘出最璀璨的光芒。
寶藏就在眼前,只是尋常人永遠看不見。
因為真正的寶藏,從來不僅僅是寶藏,而是識得寶藏之人的那一顆心。
江湖上最令人動容的傳說,永遠都與寶物有關。
寶物藏於何處?或在高山峻嶺之巔,或在大海深處幽冥。然而,最不可思議的寶藏,竟深藏於泥土之間。
楚寒山腳下的小鎮,夕陽如血,煙雲繚繞。這裡不曾出過名動天下的大俠,卻流傳著一個江湖傳說。一位老者,行將就木之際,曾言:「此地藏寶,得之者富甲天下。」
從此,小鎮便不再寧靜。
無數俠客奔赴此地,江湖好漢、名門世家、甚至市井小民,都為這一句話瘋狂。有人掘地三尺,有人深入溪澗,但尋得的,盡是黃沙碎石,終究不見寶藏的蹤影。
時日久遠,人們漸漸失望離去,楚寒山下又重歸寧靜。
但有一人未走。
他姓方,單名一個正字,江湖無名,樣貌平凡,偏偏多了一雙清亮如星辰的眼睛。他不動鏟、不動刀,只在田間漫步,眼神卻專注異常。
他看著泥土,看著稻穗,看著風吹過草地時的輕柔波紋。他凝視之處,彷彿世界都在他眼前悄然變幻。
終有一天,他蹲下身來,撿起一塊沾滿泥土的石子,拂去灰塵,嘴角微微上揚。
「找到了。」他的聲音輕柔如風。
村民們圍來看熱鬧,見他手裡不過是一塊毫不起眼的泥石,頓時哄堂大笑。
「這便是你苦尋多年的寶藏?」有人嘲諷。
方正卻微笑不語,只將石子放入懷中,轉身離去。他的步伐從容,如攜天下珍寶。
幾年後,江湖忽然傳來一個名號——方正。
他用一塊看似平凡的泥石,鑄成了一柄無雙利器,那兵刃名震天下,竟可斷金裂玉。寶劍出鞘之日,無數人恍然大悟,原來當日被世人所棄如泥土的石子,竟是世間難求的玄鐵。
而楚寒山腳下的泥土,因為蘊藏著珍貴的玄鐵礦脈,也自此成為江湖中人必爭之地。
許多人重返小鎮,意欲重尋當日的機緣,但卻再無一人能如方正般尋得真正的寶物。
人們終於明白,寶物或許人人可得,但只有那些真正看透泥土價值的人,才能從最不起眼的所在,發掘出最璀璨的光芒。
寶藏就在眼前,只是尋常人永遠看不見。
因為真正的寶藏,從來不僅僅是寶藏,而是識得寶藏之人的那一顆心。
藏在泥土中的寶物
泥土,於常人而言或許平平無奇,甚至污穢不堪。然而,於我而言,泥土卻蘊藏無價之寶,不僅是物質層面的產出,更承載着歷史、情感與回憶。
我自幼生於新界鄉郊,家門前有一片由祖父親手開墾的耕地。年少時,每逢假日便會陪同祖父下田。他常言:「這塊地,不止是種菜這麼簡單,裏面是有寶藏的!」那時的我,總誤以為泥土中埋藏着金銀財寶,滿懷好奇地用小鏟翻土尋寶。
直至某年新年前夕,我在田間無意中鏟到一個鏽蝕的鐵盒。打開盒蓋,內裡僅有一張舊照片及一封泛黃的信。祖父讀完後沉默良久,才向我道出原委:信為曾祖父於戰亂期間所寫,寄託他對流落內地的祖母的思念。鐵盒中保存的,是兩人唯一的合照與祖母贈送的髮簪,而那塊田地,正是他埋藏思念與承諾之處。
當下,我終於明白祖父口中所謂「寶藏」的真正含義。泥土中埋藏的,並非財富,而是一段跨越時代的情感、一個家族的記憶。那片泥地,孕育的不僅是作物,更承載着生命的重量與延續的價值。
歲月流轉,我離鄉赴城求學。都市生活雖精彩,卻常令人迷失。每當壓力襲來,我總想起那塊土地,回想起祖父滿手泥土的背影與那段被歲月掩埋的故事。它讓我重新找回腳踏實地的力量,亦令我明白,真正的寶藏從不光芒四射,卻能沉澱於心。
祖父辭世後,田地已荒廢,祖屋亦被改建。然而,每次歸鄉,我仍會前往那片舊地,輕觸泥土,彷彿仍可感受到過去的溫度與氣息。泥土無言,卻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與堅持,藏匿着無聲而深刻的寶藏。
泥土中的寶物,或許無法衡量其金錢價值,卻足以連繫記憶與情感。在現今物質主導的社會,回望那片沉默的土地,我更深切地領悟到,最珍貴的寶物,往往藏於最平凡之處。
泥土,於常人而言或許平平無奇,甚至污穢不堪。然而,於我而言,泥土卻蘊藏無價之寶,不僅是物質層面的產出,更承載着歷史、情感與回憶。
我自幼生於新界鄉郊,家門前有一片由祖父親手開墾的耕地。年少時,每逢假日便會陪同祖父下田。他常言:「這塊地,不止是種菜這麼簡單,裏面是有寶藏的!」那時的我,總誤以為泥土中埋藏着金銀財寶,滿懷好奇地用小鏟翻土尋寶。
直至某年新年前夕,我在田間無意中鏟到一個鏽蝕的鐵盒。打開盒蓋,內裡僅有一張舊照片及一封泛黃的信。祖父讀完後沉默良久,才向我道出原委:信為曾祖父於戰亂期間所寫,寄託他對流落內地的祖母的思念。鐵盒中保存的,是兩人唯一的合照與祖母贈送的髮簪,而那塊田地,正是他埋藏思念與承諾之處。
當下,我終於明白祖父口中所謂「寶藏」的真正含義。泥土中埋藏的,並非財富,而是一段跨越時代的情感、一個家族的記憶。那片泥地,孕育的不僅是作物,更承載着生命的重量與延續的價值。
歲月流轉,我離鄉赴城求學。都市生活雖精彩,卻常令人迷失。每當壓力襲來,我總想起那塊土地,回想起祖父滿手泥土的背影與那段被歲月掩埋的故事。它讓我重新找回腳踏實地的力量,亦令我明白,真正的寶藏從不光芒四射,卻能沉澱於心。
祖父辭世後,田地已荒廢,祖屋亦被改建。然而,每次歸鄉,我仍會前往那片舊地,輕觸泥土,彷彿仍可感受到過去的溫度與氣息。泥土無言,卻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與堅持,藏匿着無聲而深刻的寶藏。
泥土中的寶物,或許無法衡量其金錢價值,卻足以連繫記憶與情感。在現今物質主導的社會,回望那片沉默的土地,我更深切地領悟到,最珍貴的寶物,往往藏於最平凡之處。
為不完美添色彩
完美,固然令人嚮往,然而人生之所以動人,往往正因其不完美。如畫布上偶然的筆觸、陶器上的缺角、人生中的遺憾與瑕疵,都構成了獨一無二的美。學會欣賞不完美,甚至為其添上色彩,或許正是成長與生活的真諦。
中學時期,我曾參加校內壁畫創作比賽。起初,我與組員抱著對完美構圖的執念,反覆勾畫、上色,務求每一筆都準確無誤。然而在一次意外中,一位組員不慎將整罐藍色顏料潑灑於畫布一角,眾人瞬間愕然,原本細緻的構圖頓時被破壞。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不完美」,我們曾一度想要放棄重來。但經過短暫沉澱後,我們選擇換個角度思考——或許那一灘藍色,可以成為畫作的亮點。於是我們順勢將那藍色灘痕延展為夜空,添上星光與雲層,將原本白天的場景轉化為黃昏與星夜交融的畫面。
出人意表地,最終畫作奪得首獎。評審稱讚我們能靈活應對意外,將突如其來的失誤昇華為創意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不完美,並不等同失敗;若懂得接納,甚至加以轉化,不完美反而能成就獨特的美。
這份領悟亦延伸至日常生活。無論是一次不盡人意的考試成績、一段未竟的友情,抑或一次失敗的面試,這些人生中的「污點」,固然令人沮喪,但只要懷著包容與調整的心態,為它們「添色彩」,或許能化挫折為契機,從中發掘出更多可能。
正如日本傳統工藝「金繼」,匠人以金漆修補破碎陶器,讓裂痕成為美的一部分。這份將破碎轉化為美的智慧,正是為不完美添色彩的最佳寫照。與其逃避或掩飾瑕疵,不如勇敢面對,從中創造屬於自己的故事與價值。
人生如畫,不會總是平滑無礙,但正是那些意料之外的筆觸,才讓畫面更添層次與生命力。與其追求虛幻的完美,不如學會為不完美添上色彩,讓遺憾成詩,讓缺口藏光。
完美,固然令人嚮往,然而人生之所以動人,往往正因其不完美。如畫布上偶然的筆觸、陶器上的缺角、人生中的遺憾與瑕疵,都構成了獨一無二的美。學會欣賞不完美,甚至為其添上色彩,或許正是成長與生活的真諦。
中學時期,我曾參加校內壁畫創作比賽。起初,我與組員抱著對完美構圖的執念,反覆勾畫、上色,務求每一筆都準確無誤。然而在一次意外中,一位組員不慎將整罐藍色顏料潑灑於畫布一角,眾人瞬間愕然,原本細緻的構圖頓時被破壞。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不完美」,我們曾一度想要放棄重來。但經過短暫沉澱後,我們選擇換個角度思考——或許那一灘藍色,可以成為畫作的亮點。於是我們順勢將那藍色灘痕延展為夜空,添上星光與雲層,將原本白天的場景轉化為黃昏與星夜交融的畫面。
出人意表地,最終畫作奪得首獎。評審稱讚我們能靈活應對意外,將突如其來的失誤昇華為創意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不完美,並不等同失敗;若懂得接納,甚至加以轉化,不完美反而能成就獨特的美。
這份領悟亦延伸至日常生活。無論是一次不盡人意的考試成績、一段未竟的友情,抑或一次失敗的面試,這些人生中的「污點」,固然令人沮喪,但只要懷著包容與調整的心態,為它們「添色彩」,或許能化挫折為契機,從中發掘出更多可能。
正如日本傳統工藝「金繼」,匠人以金漆修補破碎陶器,讓裂痕成為美的一部分。這份將破碎轉化為美的智慧,正是為不完美添色彩的最佳寫照。與其逃避或掩飾瑕疵,不如勇敢面對,從中創造屬於自己的故事與價值。
人生如畫,不會總是平滑無礙,但正是那些意料之外的筆觸,才讓畫面更添層次與生命力。與其追求虛幻的完美,不如學會為不完美添上色彩,讓遺憾成詩,讓缺口藏光。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時常面對選擇:應否挑戰極限、勇於突破,抑或應審慎行事、量力而為?「行事要量力而為,勉強沒有好結果」與「要踏出舒適圈,才可以突破能力的界限」這兩種看法,表面看似矛盾,實則並非對立,而是須因時制宜、互為補足的處世之道。
「量力而為」強調根據自身的實際能力作出判斷與行動,避免因盲目冒進而招致失敗或傷害。在現實生活中,過度勉強往往會導致反效果。例如,學生若不顧基礎薄弱,強行報讀難度過高的課程,既可能無法應付課業壓力,亦可能打擊信心,最終得不償失。此觀點提醒我們認清自身狀況,懂得設限與保護自己,從而穩步發展。
然而,若只停留在「量力」的範圍之內,亦可能陷入自我設限的局限。「踏出舒適圈」則鼓勵人們不滿足於現況,嘗試挑戰新的領域,從而拓展視野與潛能。事實上,許多成就非凡的人物,皆是在困難與不安中成長。舉例而言,一位內向的學生若願意嘗試參與辯論隊,即使初時表現生澀,但經過多次實戰與磨練,往往能突破性格障礙,培養表達與應對能力。若未曾嘗試,這一切可能永遠無從得知。
兩者的關鍵在於一個「度」字:不盲目勉強,也不自我設限。理想的做法應是審時度勢,在了解自身能力的基礎上,適度挑戰,比現有能力略高一線的目標。如同健身訓練,若負重過重,會損傷肌肉;但若始終不肯加重,肌力則無從增強。成長與穩健之間,從來是一場動態的平衡。
總括而言,「量力而為」與「踏出舒適圈」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人生中應靈活運用的兩種智慧。在確保基本能力與心理狀態可承受的前提下,勇於挑戰、敢於嘗試,方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踏出屬於自己的一條進步之路。
「量力而為」強調根據自身的實際能力作出判斷與行動,避免因盲目冒進而招致失敗或傷害。在現實生活中,過度勉強往往會導致反效果。例如,學生若不顧基礎薄弱,強行報讀難度過高的課程,既可能無法應付課業壓力,亦可能打擊信心,最終得不償失。此觀點提醒我們認清自身狀況,懂得設限與保護自己,從而穩步發展。
然而,若只停留在「量力」的範圍之內,亦可能陷入自我設限的局限。「踏出舒適圈」則鼓勵人們不滿足於現況,嘗試挑戰新的領域,從而拓展視野與潛能。事實上,許多成就非凡的人物,皆是在困難與不安中成長。舉例而言,一位內向的學生若願意嘗試參與辯論隊,即使初時表現生澀,但經過多次實戰與磨練,往往能突破性格障礙,培養表達與應對能力。若未曾嘗試,這一切可能永遠無從得知。
兩者的關鍵在於一個「度」字:不盲目勉強,也不自我設限。理想的做法應是審時度勢,在了解自身能力的基礎上,適度挑戰,比現有能力略高一線的目標。如同健身訓練,若負重過重,會損傷肌肉;但若始終不肯加重,肌力則無從增強。成長與穩健之間,從來是一場動態的平衡。
總括而言,「量力而為」與「踏出舒適圈」並非相互排斥,而是人生中應靈活運用的兩種智慧。在確保基本能力與心理狀態可承受的前提下,勇於挑戰、敢於嘗試,方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踏出屬於自己的一條進步之路。
試吓再用魯迅嘅文筆寫一篇

篇篇都唔同真係好癲
## 泥土中的寶藏
泥土裡的東西,向來是不為人所重視的。人們走過田埂,踏過小徑,何曾低頭細看那黑褐色的土塊?然而,泥土中確有寶藏,只是埋得深些,須得彎腰去尋。這寶藏不僅是那些能吃的作物,更是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與情感。泥土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將無數故事深埋其中,等待有心人來發掘。
我幼時住在鄉下,常見農人弓著背,在田裡刨挖。他們粗糙的手指插入泥土,翻攪著,竟能掘出些紅薯、花生之類。那些作物沾著土,模樣不甚好看,但洗淨了煮來吃,卻格外香甜。我想,這便是泥土中的寶藏了罷。記得有一次,我跟著祖父去挖紅薯,他教我如何辨認泥土的濕度,如何避開那些已經腐爛的塊莖。祖父的手掌佈滿老繭,卻能準確地感知泥土的溫度與濕度,彷彿與土地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繫。他說:"土地最誠實,你對它好,它就回報你。"如今想來,這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智慧?
後來讀書,知道古時有個叫陶淵明的人,不愛做官,偏愛種豆南山下。他的詩裡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想必也是從泥土中尋得了什麼。菊花算不得什麼名貴花草,生在籬下,混在雜草中,若不是有心人,誰會去採?然而他採了,還寫入詩中,傳了千百年。泥土中的東西,有時竟比金玉還長久些。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寫道:"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這種與泥土為伴的生活,看似平淡,卻蘊含著無窮的樂趣。我想,他一定在泥土中找到了某種永恆的東西,那是遠離官場紛爭後的心靈歸宿。
城裡的公園中,常見園丁栽花。他們將名貴的花種在精緻的花壇裡,日日澆水,時時修剪。花開時,遊人爭相拍照;花謝了,便無人問津。而路邊的野花,無人栽種,無人照料,只靠著泥土中的一點養分,自開自落。開時無人賞,落時無人惜,卻也年復一年地開著。泥土給予它們的,不過是微末的養料,它們回報泥土的,卻是整個生命。這些野花讓我想起小時候見過的蒲公英,它們隨風飄散,落在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沒有人特意栽培它們,但它們卻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在不起眼的角落綻放自己的美麗。這或許就是泥土賦予它們的力量,一種不依賴外界的生命力。
有一年回鄉,見老屋後的棗樹還在。那樹生得不高,枝幹扭曲,結的棗子也小,比不上市面上的大棗甜美。但兒時我們兄弟姐妹常在樹下撿棗,棗子落在泥土上,沾了土,擦一擦便吃。如今樹還在,結的棗依然小而澀,卻再無人撿拾了。泥土中的棗樹,泥土上的棗子,竟成了無人問津的寶藏。站在樹下,我彷彿又聽見了童年的歡笑聲,看見兄弟姐妹們爭搶棗子的場景。那些簡單的快樂,如今想來是多麼珍貴。這棵棗樹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也見證了時光的流逝。它就像一個沉默的守護者,將我們的記憶深藏在年輪裡。
泥土中的寶藏,不單是那些能吃的作物,更是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農人彎腰耕作的身影,孩童赤腳奔跑的歡笑,老人坐在門檻上抽菸的沉默,都埋在泥土裡了。而今人走在柏油路上,踩著堅硬的地面,再難觸及那些柔軟的、溫熱的泥土中的事物。現代人追求效率與速度,卻失去了與土地親近的機會。我們吃著超市裡包裝精美的蔬菜水果,卻不知道它們是如何生長出來的;我們住在鋼筋混凝土的高樓裡,卻忘記了腳踏實地的感覺。
記得去年參觀一個陶瓷展覽,看著那些精美的瓷器,不禁感嘆工匠們的巧手。但更讓我感動的是解說員的一句話:"所有的瓷器都來自泥土,經過火的淬煉,才能成為藝術品。"這讓我想起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嗎?我們都來自泥土,經歷生活的磨練,最終成為獨特的個體。泥土不僅孕育了萬物,也見證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遠古的陶器到現代的建築,無一不是泥土的饋贈。
泥土不言,只是默默地藏著它的寶藏,等有心人來尋。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或許我們都應該偶爾停下腳步,彎下腰來,觸摸一下腳下的泥土。那裡藏著我們遺忘的過去,也孕育著未來的希望。當我們重新與土地建立連結時,或許能找到內心真正的平靜與滿足。畢竟,我們都是大地的孩子,終將回歸泥土的懷抱。

## 泥土中的寶藏
泥土裡的東西,向來是不為人所重視的。人們走過田埂,踏過小徑,何曾低頭細看那黑褐色的土塊?然而,泥土中確有寶藏,只是埋得深些,須得彎腰去尋。這寶藏不僅是那些能吃的作物,更是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與情感。泥土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將無數故事深埋其中,等待有心人來發掘。
我幼時住在鄉下,常見農人弓著背,在田裡刨挖。他們粗糙的手指插入泥土,翻攪著,竟能掘出些紅薯、花生之類。那些作物沾著土,模樣不甚好看,但洗淨了煮來吃,卻格外香甜。我想,這便是泥土中的寶藏了罷。記得有一次,我跟著祖父去挖紅薯,他教我如何辨認泥土的濕度,如何避開那些已經腐爛的塊莖。祖父的手掌佈滿老繭,卻能準確地感知泥土的溫度與濕度,彷彿與土地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繫。他說:"土地最誠實,你對它好,它就回報你。"如今想來,這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智慧?
後來讀書,知道古時有個叫陶淵明的人,不愛做官,偏愛種豆南山下。他的詩裡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想必也是從泥土中尋得了什麼。菊花算不得什麼名貴花草,生在籬下,混在雜草中,若不是有心人,誰會去採?然而他採了,還寫入詩中,傳了千百年。泥土中的東西,有時竟比金玉還長久些。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寫道:"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這種與泥土為伴的生活,看似平淡,卻蘊含著無窮的樂趣。我想,他一定在泥土中找到了某種永恆的東西,那是遠離官場紛爭後的心靈歸宿。
城裡的公園中,常見園丁栽花。他們將名貴的花種在精緻的花壇裡,日日澆水,時時修剪。花開時,遊人爭相拍照;花謝了,便無人問津。而路邊的野花,無人栽種,無人照料,只靠著泥土中的一點養分,自開自落。開時無人賞,落時無人惜,卻也年復一年地開著。泥土給予它們的,不過是微末的養料,它們回報泥土的,卻是整個生命。這些野花讓我想起小時候見過的蒲公英,它們隨風飄散,落在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沒有人特意栽培它們,但它們卻能頑強地生存下來,在不起眼的角落綻放自己的美麗。這或許就是泥土賦予它們的力量,一種不依賴外界的生命力。
有一年回鄉,見老屋後的棗樹還在。那樹生得不高,枝幹扭曲,結的棗子也小,比不上市面上的大棗甜美。但兒時我們兄弟姐妹常在樹下撿棗,棗子落在泥土上,沾了土,擦一擦便吃。如今樹還在,結的棗依然小而澀,卻再無人撿拾了。泥土中的棗樹,泥土上的棗子,竟成了無人問津的寶藏。站在樹下,我彷彿又聽見了童年的歡笑聲,看見兄弟姐妹們爭搶棗子的場景。那些簡單的快樂,如今想來是多麼珍貴。這棵棗樹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也見證了時光的流逝。它就像一個沉默的守護者,將我們的記憶深藏在年輪裡。
泥土中的寶藏,不單是那些能吃的作物,更是那些被遺忘的記憶。農人彎腰耕作的身影,孩童赤腳奔跑的歡笑,老人坐在門檻上抽菸的沉默,都埋在泥土裡了。而今人走在柏油路上,踩著堅硬的地面,再難觸及那些柔軟的、溫熱的泥土中的事物。現代人追求效率與速度,卻失去了與土地親近的機會。我們吃著超市裡包裝精美的蔬菜水果,卻不知道它們是如何生長出來的;我們住在鋼筋混凝土的高樓裡,卻忘記了腳踏實地的感覺。
記得去年參觀一個陶瓷展覽,看著那些精美的瓷器,不禁感嘆工匠們的巧手。但更讓我感動的是解說員的一句話:"所有的瓷器都來自泥土,經過火的淬煉,才能成為藝術品。"這讓我想起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嗎?我們都來自泥土,經歷生活的磨練,最終成為獨特的個體。泥土不僅孕育了萬物,也見證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遠古的陶器到現代的建築,無一不是泥土的饋贈。
泥土不言,只是默默地藏著它的寶藏,等有心人來尋。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或許我們都應該偶爾停下腳步,彎下腰來,觸摸一下腳下的泥土。那裡藏著我們遺忘的過去,也孕育著未來的希望。當我們重新與土地建立連結時,或許能找到內心真正的平靜與滿足。畢竟,我們都是大地的孩子,終將回歸泥土的懷抱。
冇一條DSE考試題目係AI唔識答
成個DSE可以摺埋
成個DSE可以摺埋
AI 救唔救到 大文豪篇文 ? 


今天不小心把心愛的水杯打碎了
事後我用了十五分鐘去細心欣賞
發現打碎了的玻璃碎
竟然比起平日那個形態更美
然後我再用了十分鐘去打掃地方
再為其拍照
這短短的三十分鐘
算是今天我思緒最安穩的時間
打碎了的水杯
是我今天看過最美好的東西
而那水杯著地的那一聲
是聽過最美好的聲音
原來人生覺得最爛的事情
也未必是最糟
因為最糟的
可能一直就在眼前而未曾發現
又或者根本就是自己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為不完美添色彩
教室裡的空氣悶熱而曖昧,窗外是夏日午後的蟬鳴,教室內卻只有曉雯和子豪兩人。期末考結束後,大多數同學早已離開校園,留下他們負責整理美術社的畫具。曉雯低頭擦拭著畫架,長髮不小心滑落,遮住了她微紅的臉頰。子豪站在一旁,手裡拿著一罐顏料,目光卻不自覺地停在她身上。
「你畫畫的時候,總是那麼認真。」子豪突然開口,聲音低沉,帶著一絲試探。曉雯抬頭,笑了笑,「哪有,我的畫總有點瑕疵,不像你,線條總是那麼完美。」她指的是子豪那雙擅長勾勒人體的手,他的素描總能抓住最細微的情緒,讓人臉紅心跳。
子豪走近一步,放下手中的顏料罐,輕聲說:「不完美才有趣啊,就像你。」他的手指不經意地碰觸到曉雯的手背,溫熱的觸感讓她心跳加速。她想抽回手,卻被他輕輕握住。「子豪,別鬧了……」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卻沒真的掙脫。
「我沒鬧。」子豪的眼神變得炙熱,他俯下身,嘴唇幾乎要貼上她的耳廓,「你知道嗎?我一直想為你的不完美添點色彩。」曉雯還沒反應過來,他的手已經滑到她的腰間,輕輕一拉,她整個人跌進他的懷裡。畫架上的畫布應聲倒地,顏料灑了一地,像極了他們即將失控的情緒。
曉雯的制服襯衫被汗水浸濕,隱約透出內衣的輪廓。子豪的手指靈巧地解開她第一顆鈕扣,露出一片白皙的肌膚。他低頭吻下去,溫熱的唇在她鎖骨上流連,曉雯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吟。她試圖推開他,卻發現自己的手不知何時已經攀上他的肩膀,指尖嵌入他的背肌。
「這裡是教室……」她喘息著說,聲音裡卻帶著一絲期待。子豪抬起頭,嘴角勾起一抹壞笑,「那又怎樣?不完美的地方,才更刺激。」他一把將她推到靠窗的桌子上,桌上的畫筆和紙張散落一地。他掀起她的裙子,手指沿著她的大腿內側緩慢滑動,曉雯咬緊嘴唇,試圖壓抑住即將溢出的聲音。
窗外的陽光灑進來,照在他們交纏的身影上,像一幅未完成的畫。子豪的手探進她的底線,溫柔卻帶著侵略性地撫弄,曉雯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她閉上眼,腦海裡閃過自己畫過的那些不完美的線條——歪斜、斷裂,卻在這一刻被他填滿了色彩。
「子豪……」她低聲喚他的名字,聲音裡滿是掙扎與渴望。他沒有停下,反而更深入地探索她的敏感,另一隻手解開自己的皮帶。教室裡的空氣變得更加濃烈,汗水與顏料的氣味混雜在一起,曉雯感覺自己像一張被肆意塗抹的畫布,每一筆都帶著他的溫度。
當他終於進入她時,曉雯緊緊抓住桌沿,指甲幾乎嵌入木頭。她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充實,那些她曾經自卑的不完美——畫技的生澀、身材的瑕疵,甚至是內心的羞怯——都在這一刻被他染上濃烈的色彩。子豪的動作越來越急促,兩人的喘息交織成一首無聲的樂曲,窗外的蟬鳴彷彿也在為他們伴奏。
最後的瞬間,曉雯幾乎要昏厥過去,她感覺自己像一幅完成的作品,雖然邊緣依然粗糙,卻因為他的存在而變得鮮活。子豪在她耳邊低語:「不完美,才是我們的顏色。」
教室恢復平靜,畫具散落一地,曉雯靠在子豪懷裡,看著窗外漸暗的天色。她知道,這段秘密將成為她生命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教室裡的空氣悶熱而曖昧,窗外是夏日午後的蟬鳴,教室內卻只有曉雯和子豪兩人。期末考結束後,大多數同學早已離開校園,留下他們負責整理美術社的畫具。曉雯低頭擦拭著畫架,長髮不小心滑落,遮住了她微紅的臉頰。子豪站在一旁,手裡拿著一罐顏料,目光卻不自覺地停在她身上。
「你畫畫的時候,總是那麼認真。」子豪突然開口,聲音低沉,帶著一絲試探。曉雯抬頭,笑了笑,「哪有,我的畫總有點瑕疵,不像你,線條總是那麼完美。」她指的是子豪那雙擅長勾勒人體的手,他的素描總能抓住最細微的情緒,讓人臉紅心跳。
子豪走近一步,放下手中的顏料罐,輕聲說:「不完美才有趣啊,就像你。」他的手指不經意地碰觸到曉雯的手背,溫熱的觸感讓她心跳加速。她想抽回手,卻被他輕輕握住。「子豪,別鬧了……」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卻沒真的掙脫。
「我沒鬧。」子豪的眼神變得炙熱,他俯下身,嘴唇幾乎要貼上她的耳廓,「你知道嗎?我一直想為你的不完美添點色彩。」曉雯還沒反應過來,他的手已經滑到她的腰間,輕輕一拉,她整個人跌進他的懷裡。畫架上的畫布應聲倒地,顏料灑了一地,像極了他們即將失控的情緒。
曉雯的制服襯衫被汗水浸濕,隱約透出內衣的輪廓。子豪的手指靈巧地解開她第一顆鈕扣,露出一片白皙的肌膚。他低頭吻下去,溫熱的唇在她鎖骨上流連,曉雯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吟。她試圖推開他,卻發現自己的手不知何時已經攀上他的肩膀,指尖嵌入他的背肌。
「這裡是教室……」她喘息著說,聲音裡卻帶著一絲期待。子豪抬起頭,嘴角勾起一抹壞笑,「那又怎樣?不完美的地方,才更刺激。」他一把將她推到靠窗的桌子上,桌上的畫筆和紙張散落一地。他掀起她的裙子,手指沿著她的大腿內側緩慢滑動,曉雯咬緊嘴唇,試圖壓抑住即將溢出的聲音。
窗外的陽光灑進來,照在他們交纏的身影上,像一幅未完成的畫。子豪的手探進她的底線,溫柔卻帶著侵略性地撫弄,曉雯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她閉上眼,腦海裡閃過自己畫過的那些不完美的線條——歪斜、斷裂,卻在這一刻被他填滿了色彩。
「子豪……」她低聲喚他的名字,聲音裡滿是掙扎與渴望。他沒有停下,反而更深入地探索她的敏感,另一隻手解開自己的皮帶。教室裡的空氣變得更加濃烈,汗水與顏料的氣味混雜在一起,曉雯感覺自己像一張被肆意塗抹的畫布,每一筆都帶著他的溫度。
當他終於進入她時,曉雯緊緊抓住桌沿,指甲幾乎嵌入木頭。她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充實,那些她曾經自卑的不完美——畫技的生澀、身材的瑕疵,甚至是內心的羞怯——都在這一刻被他染上濃烈的色彩。子豪的動作越來越急促,兩人的喘息交織成一首無聲的樂曲,窗外的蟬鳴彷彿也在為他們伴奏。
最後的瞬間,曉雯幾乎要昏厥過去,她感覺自己像一幅完成的作品,雖然邊緣依然粗糙,卻因為他的存在而變得鮮活。子豪在她耳邊低語:「不完美,才是我們的顏色。」
教室恢復平靜,畫具散落一地,曉雯靠在子豪懷裡,看著窗外漸暗的天色。她知道,這段秘密將成為她生命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