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2015年3月14日廣州講座
一戰這個時間節點,這個節點對於歐洲讀者來說應該是很熟悉的,對於他們來說,可以說,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文明的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對於中國讀者來說,至少對中國受現代教育產生出來的讀者來說,這個想法可能比較陌生,好像直接影響不如二戰。但是因為世界的動力中心在歐洲,世界體系的演化源也在歐洲,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視野的話,還是必須要重視一戰。

一戰是一個轉折點,它截斷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和短暫的二十世紀。這個劃分我得解釋一下。什麼叫「漫長的十九世紀」,就是,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也有人把它稱之為英國主導的世紀,或者叫做自由主義世紀,或者叫做資本主義世紀,也可以叫做殖民主義世紀。
其實這幾個稱呼有內在的聯繫。拿破崙戰爭,等於是歐洲各國內部之間模式演變的最後一次對決,以英國為代表的立憲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國和法國大革命的法國,以及拿破崙,本身就代表了拒絕這種模式的一種企圖。他們,也可以這麼說,是認為:絕對主義王權,或者是群眾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崙這樣以軍事光榮為代表的,復活古羅馬的體制,能夠給人類歷史提供另外一個出路。

但是在拿破崙最後失敗以後,法國自己也漸漸走上了英國那種議會制和資本主義制的模式,等於是挑戰者不復存在了,英國模式變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選擇。基本上所有國家,在整個十九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候,都在模仿英國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逐漸變成一個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時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過程我們通常稱之為殖民主義。

因為中國人往往用情緒化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覺得殖民主義是屈辱的,所以對這一點中國人沒有較好的理解。但是你從整個世界文明的角度來說看,可以說是,在沒有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廣大的亞非拉地區,殖民主義是迅速引進歐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見、最經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紀它毫無疑問是主流方式。
歐洲內部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過程,和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是基本同構的。這種同構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崙戰爭以前,英法爭霸,歐洲內部的國際協調沒有搞好的情況下,對外的殖民擴張不能夠有效的產生。例如,像阿蘭•佩雷菲特這樣的人會有一個,在歐洲可以說是常識的觀點,就是說,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40年發生,不是偶然的,是因為拿破崙戰爭的緣故。如果不是拿破崙的話,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經爆發了。因為英法戰爭牽制了英國東向發展的勢力,使英法兩國的勢力都留在歐洲,所以大清帝國才暫時沒有遭到印度的厄運。如果拿破崙戰爭延長一點,鴉片戰爭可能還會再延遲。
[img]
 [/img]
[/img]這就是殖民主義和歐洲內部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地方。維也納會議,結束了拿破崙戰爭造成的混亂,在歐洲內部達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國際協調的狀態,在這種國際協調的狀態下,大部分的國際糾紛可以通過列強內部協調來解決,即使真的發生糾紛的話,爆發一場戰爭,這個戰爭也是有限、有節制的。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像這樣的戰爭是費厄潑賴(Fairplay)的、小規模的、紳士的戰爭,他必須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則,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性很小,基本上不會打亂資本主義大發展。在這個有效的國際框架的約束之下,歐洲國家內部的衝突是低烈度的,歐洲國家對外的擴張是勢如破竹的,資本主義向全世界迅速發展。這就是漫長的十九世紀,或者是資產階級世紀,或者叫做英國主導的世紀。


 如果你是中國歷史學教育出來的人,那麼你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人民的生活好壞,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緣故。你看《大國崛起》或者是什麼電視片,都是傳播這種觀點,他們說,英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法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或者是實行了什麼政治制度,然後就強起來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麼人採取了什麼錯誤的政策,所以他們就弱下去了。
如果你是中國歷史學教育出來的人,那麼你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人民的生活好壞,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緣故。你看《大國崛起》或者是什麼電視片,都是傳播這種觀點,他們說,英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法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或者是實行了什麼政治制度,然後就強起來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麼人採取了什麼錯誤的政策,所以他們就弱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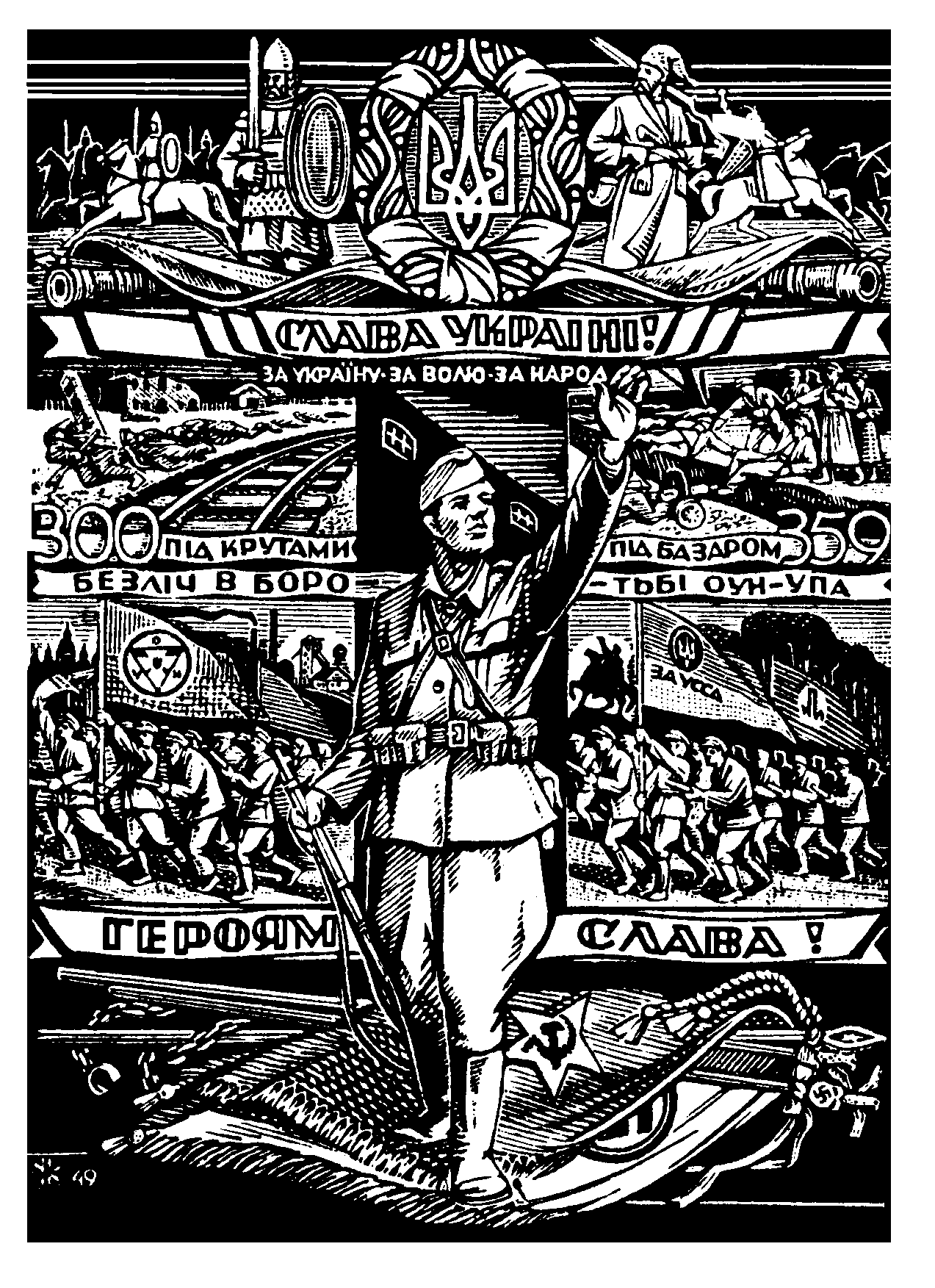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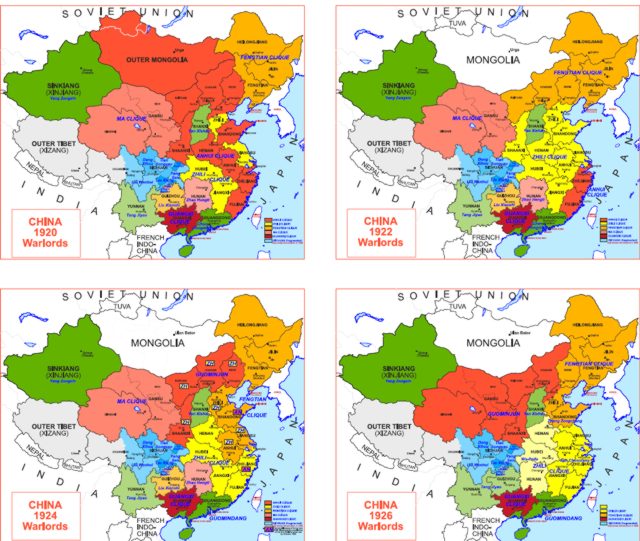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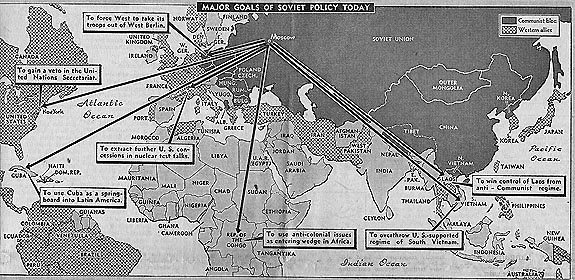




 如果推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那麼歷史教科書又要重寫了:「蘇聯是正確的,毛澤東是錯誤的。」但是我們繼續跟著毛澤東的路線去反對蘇聯聯合美國,我們豈不是更加錯誤?如果我們聯合美國反對蘇聯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徹底否認毛澤東了。
如果推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那麼歷史教科書又要重寫了:「蘇聯是正確的,毛澤東是錯誤的。」但是我們繼續跟著毛澤東的路線去反對蘇聯聯合美國,我們豈不是更加錯誤?如果我們聯合美國反對蘇聯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徹底否認毛澤東了。







 他們會設立一些假想,比如說,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是人民的進步,或者是世界革命之類的假想的價值觀,對於真實世界的政治面目,影響是幾乎可以不提的。你如果相信他們的結論的話,那不會改善你的處境,只能夠增加你的認知錯誤,使你付出重大的代價。謝謝。
他們會設立一些假想,比如說,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是人民的進步,或者是世界革命之類的假想的價值觀,對於真實世界的政治面目,影響是幾乎可以不提的。你如果相信他們的結論的話,那不會改善你的處境,只能夠增加你的認知錯誤,使你付出重大的代價。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