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但亦有好多你根本唔會跟個部首去學隻字
漢字在最初只有象形指事階段時,確實有可能有一段純粹的表意期。不過這段時間恐怕不長-至少不在我們熟悉的古文獻裡。例如隨手翻開中國春秋時期的文字記錄,已經出現許多形聲字及做為語法使用的虛詞,且以漢字音轉譯記錄的《越人歌》也證明了當時的漢字已於音聲語言連結。
事實上,漢字中的形聲字-也就是依存發音的字,佔整體漢字中約八成之多。所謂的形聲字,便是以形符和聲符兩部分組成,正因為形聲字如此之多,我們也才可以遇到不會的字時「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
既然有象徵意義的形符,不就一定程度表達了意義了嗎?但即便形聲字具備了形符,但意義的「區別」仍多透過與音聲語言的連結建立。舉例來說,不認識「梧」的人看到木字邊可以知道這可能是一種植物,而「桐」也可以。那「植」也是如桐樹一樣的一種植物嗎?「標」呢?
我們當然可以說,在這些字草創時期,這些都是植物「相關」的字。但其一,我們看不出他相關在哪,可能是一種植物名,也可能是樹的末端,更可能是木材的某種製品;其二,之所以右邊的聲符會是該聲符,便是因為在此字誕生之時,那個「概念」的語音是右邊聲符的音。但是語音變化快速,而今我們不但感覺不到「標」的「票」音是對應哪個單詞,更不是先了解「標」的古義再去認識「標準」這個詞的意思。
拿英語對比的話,給英語使用者一個沒看過的字-就例如 ganbarism 好了,他們可以從詞尾過濾出這個字大概不是一種魚或一個身體部位、而是一種抽象概念,但是無法特定至某一個精確的意義。在這個層面上,漢字使用者和其他表音文字使用者並沒有太大區別。
正因如此,語源和文字學才會如此有趣。如果我們還是一看就知道這個漢字代表什麼、是什麼意思,那麼我們可能就再也不覺得這些故事新鮮了。
嚴格說來,漢字並不是「表意」的系統。在語言學上,現代漢字這種系統稱作「語素文字」(Logogram/Logograph)。一個字代表一個「語素」,與語言的「詞」有著嚴格的對應關係,記錄的還是語言,並依存著語言。
那有沒有真正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有不同語言使用者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的文字?歷史上曾經有許多學者為此做了許多嘗試,也就是創造出真正不依存任何語言的客觀文字,例如弗雷格在1897年出版的《概念文字》,便試圖創造出一套依存視覺而不依任何語言的文字。這套系統在邏輯及哲學上是很好的材料,但成為不了大家通用的「語言」。
除了弗雷格外,奧地利的哲學家紐拉特也曾試圖以圖形製出世界通用的「國際圖形文字」,只是後來仍以失敗告終。其原因主要在於,不依存語言的文字,多只能表示較有共通性的名詞,一旦遇上複雜的概念便束手無策。
換句話說,漢字的價值並不在於它的「表意功能」,從宏觀的角度來說,所有語言的文字序列都有「表意功能」,如英語使用者見到able結尾的字就能大概過濾出一定意義。漢字的特色在於,這些「表意功能」被包括進一個「字」,但這個特色並不讓它真的「優」於其他表記系統。
用乜中文輸入法已經知道年紀
Pinky男友
200 回覆
78 Like
571 Dislike
你唔識關我咩事💀係人都可以學打粵拼
筆劃輸入法 唔識瘋狂按*
唔識瘋狂按*
 唔識瘋狂按*
唔識瘋狂按*我真係識呢個, 仲打得幾快
蘇浙公學專用
蘇浙公學專用

gtw
pin j
gaaudim!
pin j
gaaudim!
九方
用得呢個都係蘇浙公學㗎嘞
90後...用緊蒙恬手寫板
90後速成轉倉頡

MacBook 速成

但問題係我成日唔記得佐個字點寫變佐打唔出要用語音

語音最大問題係隔離聽到你做緊咩

其實會😂
多筆畫嘅字會記得字首字尾點寫,但中間因為輸入法唔需要「用」到,會唔記得咗
多筆畫嘅字會記得字首字尾點寫,但中間因為輸入法唔需要「用」到,會唔記得咗
常用字記哂位真係打得幾順手
但有啲字唔常用要慢慢搵
我有試用過一個中文輸入法幾有趣
叫Stringboard
但明顯個輸入法未完善

但有啲字唔常用要慢慢搵
我有試用過一個中文輸入法幾有趣
叫Stringboard
但明顯個輸入法未完善

咁我又唔係講D咩機密
其實60-70後係手寫,或者唔打,直接錄音
呢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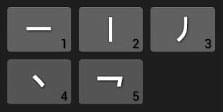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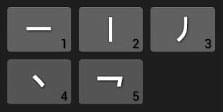
邊會唔識粵拼
睇得多香港地方名同人名嘅英文串法就自然識拼

睇得多香港地方名同人名嘅英文串法就自然識拼

我唔識都會不停按*
同埋已經打到可以唔望住鍵盤

同埋已經打到可以唔望住鍵盤

倉頡門檻太高,首先要識個字點寫,再要識取碼,雙重門檻,如果唔係學校教,無咩人識用

http://www.miniapps.hk/g6code/
《六碼筆畫》輸入法
《六碼筆畫》輸入法
睇得多香港地方名同人名嘅英文串法就自然識拼淨係你依句我都有排拼

我有時候打字快過速成

無錯 



我都仲記得點用
但由細到大用開倉頡,始終唔夠用倉頡順手




我都仲記得點用
但由細到大用開倉頡,始終唔夠用倉頡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