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imefortune/98380
要在公開場合看到毫不修飾的體毛是非常罕見的,因此就連名人露出腋毛都能成為新聞。對於一般大眾而言,即便在海邊衣服穿得非常少的情況下,露出體毛本身似乎就帶著某種特殊意涵。有越來越多女性會除去所有看得見的體毛,包含陰毛在內。而男性也不惶多讓,使得「back, sack and crack」(背部、陰囊後方和股溝)熱蠟除毛越來越受歡迎。1970年代盛行的濃密胸毛與「花花公子」般的陰毛已不復存在。簡而言之,體毛已經不再是理想體態的要件之一。
然而,所謂的「理想體態」不只是光滑無毛那麼簡單,而是「每個人、每天」都必須維持這樣的狀態。儘管我們活著的每一刻毛髮都是不斷生長的,但外露的體毛(被視為不正常和不自然)卻會讓你顯得與眾不同。 身為一名倫理學家,這種日趨流行的審美要求,以及為何會形成「經修飾的身體才是『正常』甚至『自然』體態」的風氣令我感到十足憂心,而且還不僅僅如此。
顯然地,我們付出了額外的心力來創造「正常」或「自然」。如果我們想要去除體毛,就需要更常使用剃刀、用手拔、用熱蠟除毛以及雷射等方式。(同時,當談到頭髮,我們卻希望頭髮茂密。我們還會去染髮、做造型、綁出各種花樣、接髮,甚至為了一頭飄逸秀髮而去植髮。)這樣的除毛標準是苛刻的、持續且每日不停重複的。然而卻鮮少有人意識到它的苛刻。相反地,大家都把它當成一件正常的事。
隨著光滑無毛的身體成為大眾唯一能接受的體態,一場巨變隨之產生。除毛不再是一種「美容行為」(beauty practice),它被重新定義成一種「衛生行為」(hygiene practice),成為所謂「例行保養」的一環。除毛變成一項規定和一種我們必須做的事。它不再是一個你可以拒絕的選項(如洗牙),但它卻沒有衛生行為應有的健康益處。美容行為是你隨心所欲且選擇性的;而衛生行為則是必要的。你不必一定得美容,但你一定得做點什麼來讓自己符合「正常」的最低標準。因此,一旦除毛完全變成一種例行事項,那麼它作為一種苛刻的美容行為的事實便會消失殆盡。
從為頭髮做造型、染髮、甚至每天要為頭髮擦上各種潤髮乳和護髮劑,我們可以發現有這些變化已經產生。在健康上也有所改變:有些飲食和運動習慣(如把自己練得過度壯碩,或是認為極度骨感才是健康)已經不再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美觀。更嚴重地是,儘管與事實相反,我們最終將忘了光滑無毛的身體並非最自然的體態。身體是會長毛髮的!
這在各個層面都會帶來高昂代價。隨著對美的要求增加,我們不僅得花更多時間來維繫美貌,它的本質也會有所改變。美麗變得更加重要,它開始以一種「倫理典範」的形式運作。這往往是我們最重視的(無論是非),我們思索、談論、甚至砸下大把時間和金錢來換取美麗。如果我們善於打扮和維持美貌,我們會感到滿意甚至覺得自己品德出眾;如果相反,無論我們有哪些長處,幾乎仍會覺得自己不夠好。人們也常常以貌取人,我們會以他人的外表來對其個性與成功與否妄加猜測。我們往往直接從別人的長相來解讀他的個性,而這件事其實從我們四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在此狀況下,關於體毛的批評便不再輕如鴻毛。除毛並不是「時尚」造成的錯誤,這不像在細跟高跟鞋流行時穿著厚底鞋,或是在緊身褲非常普遍時穿喇叭褲。事實上,就時尚而言,現今社會能接受的多樣性與分歧性已更甚以往。過去曾是以衣服下襬長度和剪裁手法來決定一個人是否跟上流行,但這已經不適用於今日。然而,服裝的多樣化卻隱藏了社會對於身體相似性的要求。你可能因為穿著非名牌的運動鞋而感到丟臉,但衣服畢竟不是你的身體,它們不代表你的本質。但隨著美麗成為一種倫理,對於身體的羞恥感也將成為對自我本質的羞恥,這樣的嚴重程度可見一般。
一旦這樣的模式重複下去,對美的標準與困境將會相應成長。美貌的理想典範將成為一種倫理典範,而「變美」會變成一項道德責任。現今所有的美容行為和過去相比已非那般特殊與罕見,從光療指甲、施打肉毒桿菌到玻尿酸等皆是如此。在某些地方,整形手術已是一種日常慣例——例如南韓的「眼皮年輕化手術」(blepharoplasty)或雙眼皮手術。如果這股潮流持續,許多難以達成的特徵——如光滑無毛——就會變為必要。社會對它們的要求將不是為了追求美麗或是完美,而僅是為了剛好符合社會的「正常」標準。
 有咩問題?男人有毛好正常
有咩問題?男人有毛好正常 不了!好撚噁心
不了!好撚噁心 有咩問題?男人有毛好正常
有咩問題?男人有毛好正常 不了!好撚噁心
不了!好撚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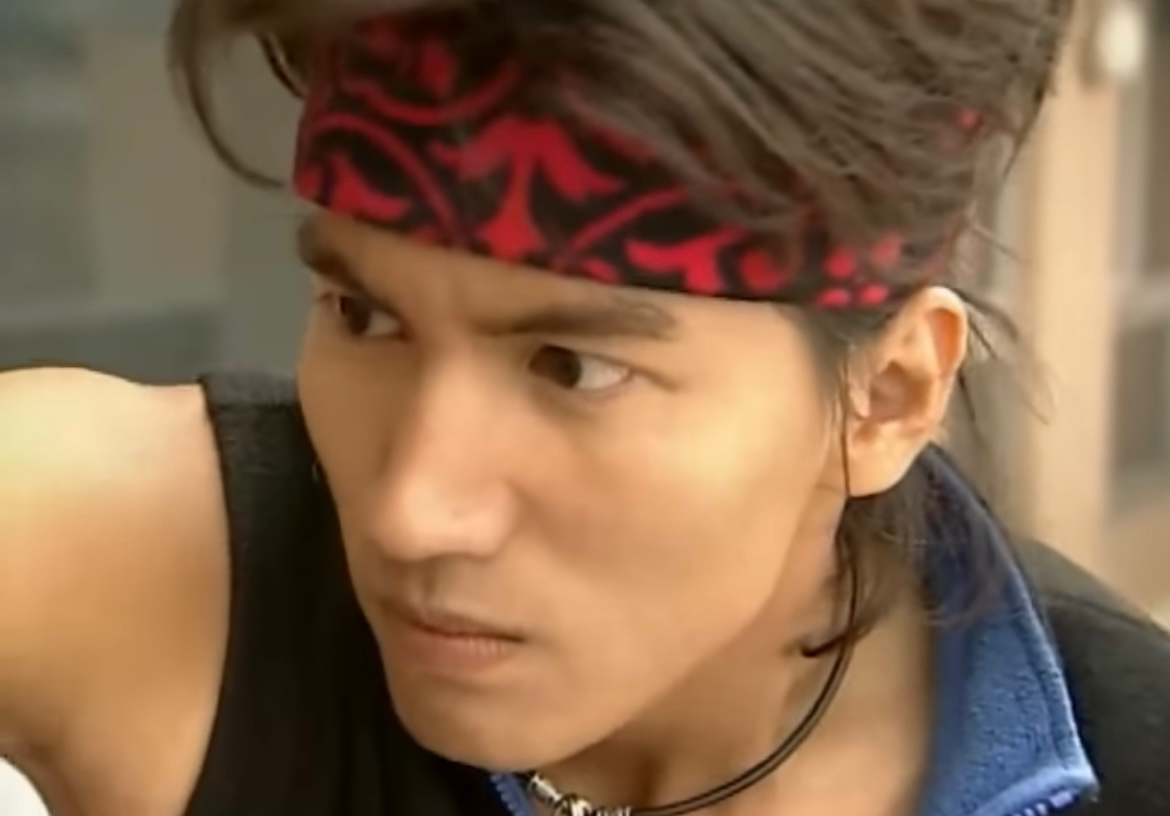






 認真想問
認真想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