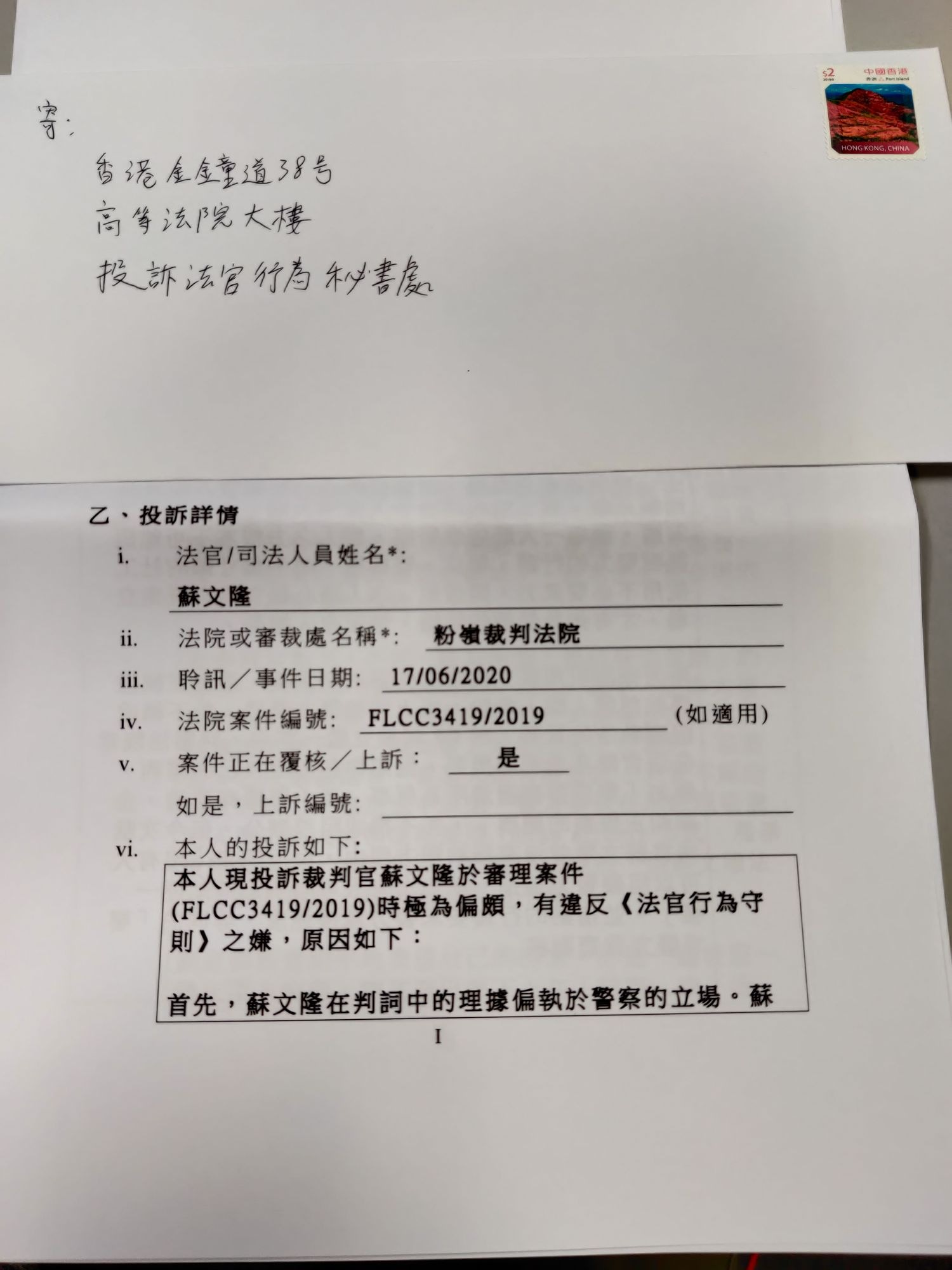香港金鐘道38號
高等法院大樓
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
*********************************************
請download投訴信 PDF/ Word Format:
https://www.judiciary.hk/zh/court_services_facilities/complaintsjjo.html
*********************************************
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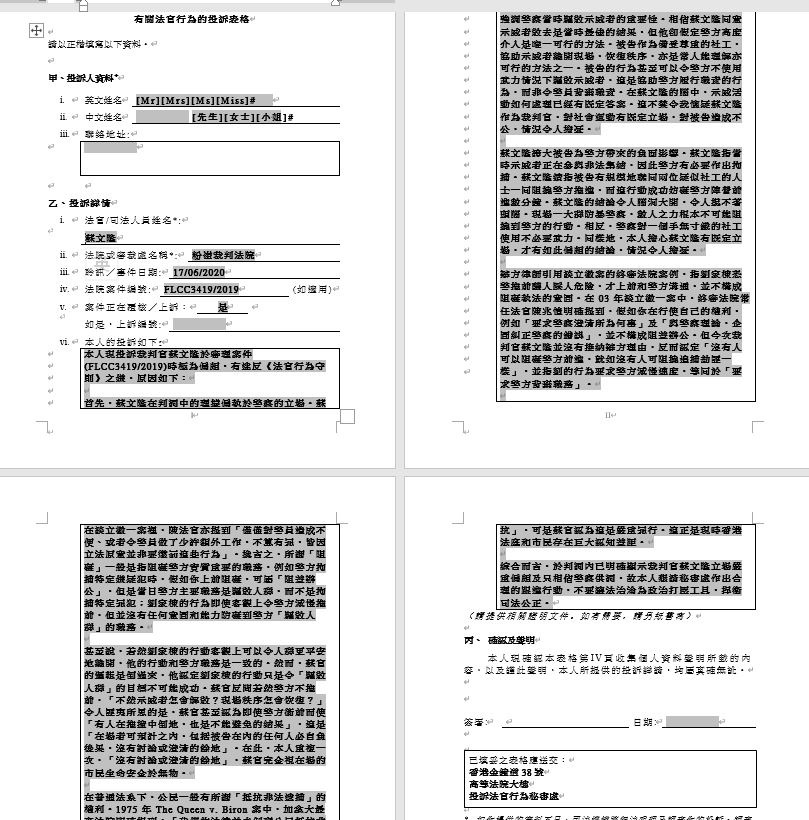
*********************************************
填寫內容
甲部 填返個人資料
乙部
法官姓名:蘇文隆
法院: 粉嶺裁判法院
案件編號:FLCC3419/2019
聆訊日期:17/06/2020
投訴內容:(有心既可以自己改下啲用字)
本人現投訴裁判官蘇文隆於審理案件(FLCC3419/2019)時極為偏頗,有違反《法官行為守則》之嫌,原因如下:
首先,蘇文隆在判詞中的理據偏執於警察的立場。蘇文隆指被告的行為阻撓警方推進,令示威者有更多時間離開,是在迫使正推進的警員背棄職責。蘇文隆亦強調警察當時驅散示威者的重要性。相信蘇文隆同意示威者散去是當時最佳的結果,但他卻假定警方高度介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被告作為備受尊重的社工,協助示威者離開現場,恢復秩序,亦是常人能理解亦可行的方法之一。被告的行為甚至可以令警方不使用武力情況下驅散示威者,這是協助警方履行職責的行為,而非令警員背棄職責。在蘇文隆的腦中,示威活動如何處理已經有既定答案。這不禁令我懷疑蘇文隆作為裁判官,對社會運動有既定立場,對被告造成不公,情況令人擔憂。
蘇文隆誇大被告為警方帶來的負面影響。蘇文隆指當時示威者正在參與非法集結,因此警方有必要作出拘捕。蘇文隆續指被告有規模地聯同兩位疑似社工的人士一同阻撓警方推進,而這行動成功妨礙警方陣營前進數分鐘。蘇文隆的結論令人腦洞大開,令人摸不著頭腦。現場一大群防暴警察,數人之力根本不可能阻撓到警方的行動。相反,警察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社工使用不必要武力。同樣地,本人擔心蘇文隆有既定立場,才有如此偏頗的結論,情況令人擔憂。
辯方律師引用談立徽案的終審法院案例,指劉家棟恐警推前釀人踩人危險,才上前和警方溝通,並不構成阻礙執法的意圖。在 03 年談立徽一案中,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明確提到,假如你在行使自己的權利,例如「要求警察澄清所為何事」及「與警察理論,企圖糾正警察的錯誤」,並不構成阻差辦公。但今次裁判官蘇文隆並沒有接納辯方理由,反而認定「沒有人可以阻礙警方前進,就如沒有人可阻撓追捕劫匪一樣」,並指劉的行為要求警方減慢速度,等同於「要求警方背棄職務」。
在談立徽一案裡,陳法官亦提到「僅僅對警員造成不便、或者令警員做了少許額外工作,不算有罪,皆因立法原意並非要懲罰這些行為」。換言之,所謂「阻礙」一般是指阻礙警方實質重要的職務,例如警方拘捕特定嫌疑犯時,假如你上前阻礙,可屬「阻差辦公」,但是當日警方主要職務是驅散人群,而不是拘捕特定罪犯;劉家棟的行為即使客觀上令警方減慢推前,但並沒有任何意圖和能力防礙到警方「驅散人群」的職務。
甚至說,若然劉家棟的行動客觀上可以令人群更平安地離開,他的行動和警方職務是一致的。然而,蘇官的邏輯是倒過來,他認定劉家棟的行動只是令「驅散人群」的目標不可能成功。蘇官反問若然警方不推前,「不然示威者怎會解散?現場秩序怎會恢復?」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蘇官甚至認為即使警方衝前而使「有人在推撞中倒地,也是不能避免的結果」,這是「在場者可預計之內,包括被告在內的任何人必自負後果,沒有討論或澄清的餘地」。在此,本人重複一次,「沒有討論或澄清的餘地」,蘇官完全視在場的市民生命安全於無物。
在普通法系下,公民一般有所謂「抵抗非法逮捕」的權利。1975 年 The Queen v. Biron 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明確提到:「我們的法律並未剝奪公民抵抗非法逮捕的權利。」假如警方的執法是不正當的、甚至是非法攻擊被捕者,當事人都有權抵抗,只要不超出過度的武力。在反送中以來,警方多次在示威現場違犯人權法地大規模胡亂逮捕 (mass arrest) 市民、濫暴攻擊被捕者,本已犯罪,亦屬非法逮捕。但蘇文隆法官卻對此事實一無所知或視而不見。
劉家棟相當和平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亦是一邊後退一邊和警方說理,這甚至已稱不上在「防礙」或「抵抗」,可是蘇官認為這是嚴重罪行。這正是現時香港法庭和市民存在巨大認知差距。
綜合而言,於判詞內已明確顯示裁判官蘇文隆立場嚴重偏頗及只相信警察供詞,故本人懇請秘書處作出合理的跟進行動,不要讓法治淪為政治打壓工具,捍衛司法公正。